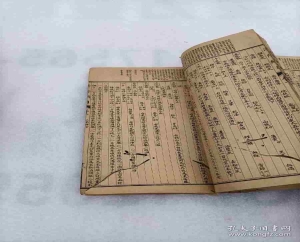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古代婚姻法律,古代女人离婚七出三不进】,以下3个关于【古代婚姻法律,古代女人离婚七出三不进】的北京法律知识分享,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北京法律知识。
离个婚就这么难,古代“离婚”政策:从七出到三不去
现在我经常听到离婚这个词。说实话,这不是一个外来的进口词,而是一个古老的词。我们能找到的最早的文字记录来自唐代方玄龄编纂的《禁书刑法志》,这表明我们现在在各国的法律统一术语和离婚词已经在晋朝国家法律中明确出现。但是离婚最始于什么时候?历史上没有准确的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从人类开始通过婚姻组,家庭就有了走出围城的做法。因此,一般来说,离婚这个词只存在于现代,但走出围城的现象早已存在,并逐渐严格规范。
即使在古代离婚,这两个词也没有出现,但根据具体情况,还有其他词可以分享这个意思。
第一个词是独一无二的,即夫妻任何一方在一定范围内殴打、虐待、伤害对方的亲属,即家庭暴力甚至杀戮,都被迫离婚。第二个词是合理的,夫妻双方都同意离婚。第三种叫做休息或早期阶段,也就是说,丈夫被迫离开妻子,虽然古代似乎更人性化,尤其是合理,但实际上是古代知道是男性社会,女性后来强调三从四美德,所以大多数只能是男人离婚,女人不允许提出。
总的来说,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远远低于今天的妇女。因此,古代男性提出走出围城的一些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在汉代,有一位名叫王的官员。找个理由是很胡说八道的。他说七曲的主人在早淡季甚至消失了。仅仅因为他的妻子摘了别人的枣子,他就被遗弃了。此外,在后汉书中,两人的比试也非常精彩。据说暴勇刘秀的大臣养育了他的继母,直到他的孝顺妻子长大于他的母亲。狗永立即去找他的妻子,也就是说,他被暴勇抛弃了,因为他在母亲面前责骂狗。另一个是东汉大臣李冲,因为他的妻子私下告诉他,妾有私人财富,愿意分义、破碎、责骂期间外出等等。现在人们似乎很难接受,私人资金也无法存入。
但通过这些例子,不要认为男人在古代可以随意终止婚姻,因为夫妻的离婚不仅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且受到家庭礼仪和合理的审判的控制。
我们可以立即在白居易集中讲述另一个真实的故事,说当一个妻子给她在田里耕种的丈夫送食物时,她在路上遇到饥饿的父亲时,她把食物给了她的父亲。她丈夫在田里焦急地叫着给你父亲吃饭。他非常生气,坚持要离婚,妻子拒绝接受,所以他起诉了政府。当时,白居易是主审,他在判决中说,根据妇女的倒退标准,妻子应该服从丈夫。然而,报答父亲的善良是出于自然的原因,所以他应该先给父亲食物。在那之后,丈夫不能休息,因为孝道比世界上的丈夫更重要。也就是说,虽然古代不是法治社会,但也不是没有原则。有时候,宗教礼仪和道德标准大于法律。
好吧,古代女性同胞受到压迫,但是也不是绝对的。
例如,在唐代,这是一个男女平等的王朝,根据保存完好的唐代妻子书,即离婚证书的内容,相当感人,内容一般分为三段,第一段重述夫妻命运,经过灾难修复,应该像鱼一样,整天快乐。
然后第二段描述了目前的情况,由于两个人的个性不同,经常发生冲突,大小不安,六个亲戚愿意,真的不能继续下去。第三段写离婚的祝福,因为不能属于同一个家庭,最好是一个不同的两个家庭每个学生快乐,同时祝福离婚后,愿母亲离开,禅宗葬礼是梅嫂子峨眉,乔城苗条的姿态,选择高级官员有自己的未来,但蚊子听起来很温暖,祝福也很美好。即使在离婚数量的结束时,有些人也会向妇女注明赡养费,离婚证明会聚集两个父母和亲戚一起作证,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离婚协议,尽量聚在一起。
唐代以后的宋朝,现在很多人认为宋朝是女性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的时代。宋明理学杀人。事实并非如此。宋代妇女的地位不仅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低,甚至在历代,宋代妇女的地位也很高。例如,宋代法律中存在妇女的财产权、离婚权、再婚权、财产继承权和财产处置权,相当完整。
所以说到这里,我们想谈谈宋代名人的真实故事。主人公要么是别人,要么是宋代女诗人婉约派的代表。被称为永恒第一个才女的李清照说,靖康之耻发生后,战争不断。赵明诚的老将不幸死于湖州,近30年的幸福婚姻结束了。李清照没有固定的住所,被迫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再婚一个叫张汝周的人。
事实上,张汝舟结婚的初衷是看中李清照丈夫留下的有价值的书法和绘画文物。当然,张汝周不想给清照看。结果,张汝周打了他的头。没有办法。李清照决定与张汝州离婚,并起诉张汝州欺骗国王。当然,判决是李清照胜诉,张汝州被分配到柳州,尽管李清照被判入狱两年,但在当地官员的照顾下,他在监狱里只坐了9天就被释放了。这样,李清照不仅在这场离婚战争中成功离婚,而且保留了他所有的财产,这得益于宋代法律规定中妇女同胞财产权的保护。如果把它放在后面的朝代,我真的不确定李清照是否能赢。
中国古代彩礼漫谈
作者:叶萍(西南政法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彩礼在古代称为聘(娉)礼或聘财,是婚约缔结的证明要件之一。从西周时期始,关于婚姻的缔结便有两个重要的社会规范:
一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滕文公下》中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从社会风俗来讲,婚姻不遵从父母之命,没有专门媒妁的提亲,是会被整个社会所鄙视的,这样的结合不被认可。
二是男方需要向女方纳聘财。据《仪礼·士婚礼》的记载,婚姻的成立有“六礼”的程序,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是指“使使者纳币以成婚礼”。“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向女方下聘财,下聘意味着婚约关系的确立,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不得随意违背婚约。
自古以来,人们就对婚姻的仪式感倍加重视。《白虎通义·嫁娶》明确指出:“女子十五许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贽。”除纳征执布帛外,其他五礼都需执雁而行,大雁代表着婚姻的坚贞不渝,这便是后来的奠雁之礼。“用雁者,取其随时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逾越也。”
清代梁永康在《冠县志》中这样描述当时的下聘之礼:“婚期前日,男家具仪物送至女家,曰通道路,喜盒二抬或四抬八抬不等,内盛首饰、布正、糖菜、干菜及酒肉、生鸡鹅类,取纳采奠雁之义,女家亦送妆奁,皆由贫富而有厚薄。”除去首饰,还用鹅代雁取古之奠雁之礼,可见传统婚俗对中国影响之深。
彩礼在周甚至周以前相对比较简单,但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彩礼也开始“水涨船高”。东汉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这样介绍当时普通人家的彩礼:“一飨之所费,破毕生之本业。”通俗地讲,就是拿彩礼的时候,一顿饭的工夫,一家一辈子攒下的钱就没了。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足以说明彩礼之高。同样,《汉书·王莽传》记载:“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可见,哪怕皇帝娶媳妇也要很高的彩礼。
唐代将聘礼作为判定婚约关系存在的重要物证。《唐律疏议·户婚》载:“婚礼先以聘财为信,故礼云:‘聘则为妻。’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在没有婚书的情形下,将男方下聘礼,女方受聘财这样的社会通俗做法也视为法律上的婚约成立,某种程度上承认聘财是婚约成立的事实要件。如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中写到:“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蘋蘩。”可见,下聘礼代表着婚姻的正式缔结。
聘礼除去是婚约成立的重要证明要件之外,也起着担保婚约履行的功能。在悔婚、妄冒(指婚礼中的冒名顶替等欺骗性行为)、违律为婚(违反法律的规定结婚)几种情形下,法律分别根据男女双方在婚姻缔结中的过失程度予刑罚处罚,以及规定过错方返还聘礼或不追聘礼。对于女方悔婚,《大明律》甚至规定女方需“倍追财礼给还”,即将“财礼”双倍返于男方。这里的“财礼”一定程度具有成婚定金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法律对聘财的认定标准相当宽松,对聘财的形式及数量并无严格的限定。如唐律中“聘财不拘重轻,但同媒约言明纳送礼仪者方是。”重要的是在形式上完成“纳征”之礼。“‘聘财无多少之限’,即受一尺以上,并不得悔。”立法者的意图非常明确,聘礼不以钱物多少为限,只要双方具有以此作为聘礼的共同认识,即为法律所认可。对聘礼的具体形式,法律并未有明确限制,可以是钱也可以是物。聘礼不论财物多寡,不论礼物之形式,但是聘礼又需要庄重雅致,以表达对婚姻的尊重。这就是唐律所说“若乡间为货之物,如巾帕之类,不得即为聘财。”
彩礼源于婚俗,而后定为制度,彩礼不仅是婚约关系存在的证明,更重要的是对婚姻缔结的担保。古代法律一开始对彩礼没有数量和形式的硬性规定,立法者肯定的是聘礼这一古老的婚姻仪式,强调婚姻的神圣性和庄严感。但是,由于妇女在传统家族制社会中并不具有独立的个体价值,传统的婚姻缔结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结婚对象的挑选并非基于情感,彩礼中的财产属性被放大,由此导致的女家待价而沽互相攀比不可避免。最终使婚姻演变为身份、等级、阶层、利益交换的较量。甚至产生最恶劣的后果,家长将女性明码标价视为婚姻市场的交易品,这种情形从封建社会漫延至民国初年仍然不止。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婚姻法制发生根本性转变,以男女两性个体独立且平等的现代婚姻法制破除“父母之命”的结婚前提,将两性“婚姻自由”视为根本原则,婚姻中的家长意志被剔除。婚姻自由意味着婚姻的缔结不受任何人干涉,法律更是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传统婚姻中彩礼对婚姻成立的担保价值也不复存在。时代发展,两性婚姻的缔结应当在基于个体独立的基础之上,回归其情感价值。“鸿雁于飞,肃肃其羽”,彩礼的意义也需要回归其仪式感的价值定位。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5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古代婚姻法制中的彩礼及其现代转型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遏制婚俗领域的不正之风,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行婚俗改革,而婚俗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是彩礼问题。受传统婚俗的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依然有男方向女方下聘礼的现象。但是在攀比虚荣的风气带动下,彩礼逐渐变味,“天价彩礼”频现,对我国婚姻领域的健康发展以及整个社会文化都带来严重危害。在此情形下,回顾彩礼在历史上的发展脉络,特别是我国古代法制中对彩礼的相关规制,引导社会重新正确认识传统婚俗及法制中彩礼的定性及价值仍有必要,特别是重塑彩礼的现代价值移风易俗有重要意义。
彩礼在古代称之为聘(娉)礼或聘财,是婚约缔结的证明要件之一
自西周时期始,关于婚姻的缔结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一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诗经·齐风·南山》中记载:“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孟子·滕文公下》中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从社会风俗来讲,婚姻若不遵从父母之命,没有专门媒妁的提亲是会被整个社会所鄙见的,这样的结合不被认可。
二是男方需要向女方纳聘财。据《仪礼·士婚礼》记载,婚姻的成立有“六礼”的程序,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是指“使使者纳币以成婚礼”,孔颖达对此注疏曰:“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向女方下聘礼,而后婚成,下聘意味着婚约关系的确立,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不得随意违背婚约。“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非受币,不交不亲”。随着时代的变迁,西周时期的婚姻六礼在各个历史时期虽有形式上的变化,但是就社会婚俗核心内容而言,人们对父母之命与聘礼婚成的认识没有改变。
古代律典并没有直接规定聘礼是婚姻缔结、成立的必要条件,但是却遵循社会风俗对聘礼的共同认知,将聘礼作为判定婚约关系存在的重要物证。受西周以来婚姻“六礼”的影响,婚姻的缔结先有婚约再有婚礼而后婚成,法律规定婚书是婚约缔结的证明要件。古代律典关于婚姻缔结的法律规范中,由于《宋刑统》同于《唐律疏议》,《大清律例》同于《大明律》,以下将详细比较唐明律的相关规定,以见其异同。《唐律疏议·户婚》曰:“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男家自悔者,不坐,不追娉财。”依照该条法律内容,婚嫁中双方订立婚书即视为婚约缔结成立,对双方产生约束力。律文下面的疏议解释道:“婚礼先以娉财为信,故礼云:‘娉则为妻。’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疏议实质上是补充规定在没有婚书的情形下,将男方下聘礼,女方受聘财这样的社会通俗做法也视为法律上的婚约成立,某种程度上承认聘财是婚约成立的事实要件。《大明律》的内容与唐律的规定整体上是一致的,“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疾残、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一是从立法技术的层面将疏议中关于聘财的内容直接写进律条;二是不再仅将聘礼视为婚约成立的证明,而是直接将聘礼视为婚姻订立的必备仪式。
值得注意的是,唐律对聘财的认定标准相当宽松,对聘财的形式及数量并无严格的限定,立法者意在保留及尊重聘礼这一传统婚俗。疏议进一步解释“聘财不拘重轻,但同媒约言明纳送礼仪者方是。”重要的是在形式上完成“纳征”之礼。疏议中继续规定:“‘娉财无多少之限’,即受一尺以上,并不得悔。酒食非者,为供设亲宾,便是众人同费,所送虽多,不同娉财之限。若‘以财物为酒食者’,谓送钱财以当酒食,不限多少,亦同娉财。”立法者的意图非常明确,聘礼不以钱物多少为限,只要双方具有以此作为聘礼的共同认识,即为法律所认可。对聘礼的具体形式,疏议并未有明确限制,可以是钱也可以是物,但是以列举的方式排除了“酒食”之类的食物类消费品,认为其为供设宾客之用,不属于聘礼。但是如果所送聘财作为婚宴酒食之目的,又不限多少,等同聘财。聘礼不论财物多寡,不论礼物之形式,但是聘礼又需要庄重雅致以表达对婚姻的尊重。疏议还有如此规定“若乡间为货之物,如巾帕之类,不得即为聘财。”这再一次表明法律对待聘礼之态度,是对古老民俗的尊重,也是通过聘礼这种形式传达对婚姻的珍重。
当婚姻缔结失败时,法律对聘礼返还有完备的规定,聘礼可以作为对违约方的惩罚措施以及对另一方的补偿手段
传统聘礼又具有担保婚约履行的功能。
第一种情形:悔婚。法律分别规定男女双方的悔婚惩罚及聘财返还情况。唐律规定:(1)女方在已有婚书私约或者受聘财的情形下悔婚,除去处以杖六十之刑外,还得将婚约履行完毕。(2)女方将女另许他人还未成婚,处以杖一百之刑。女方追归前夫,如果前夫不娶,女方须返还聘财,与后夫婚成。(3)女方另许他人,婚姻已成,处以徒一年半之刑,返还聘财。明清律为进一步保护婚约的有效性,加重打击悔婚,特别是加重处罚女方悔婚的情形。
《大明律·户婚》“男女婚姻”条稍有差异:“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谓先已知夫身残疾、老幼、庶养之类)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婚者,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财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大明律减轻了悔婚的刑事惩罚力度,但是却加重女方的民事责任,如果另许他人之后前夫不愿成婚,则女方需“倍追财礼给还”即将聘财双倍返于男方,这里的聘财一定程度具有了成婚定金的性质。对男方悔婚而言唐律规定“男家自悔者,不坐,不追聘财”;但是明律除规定不追聘财外,男方悔婚罪同女方:“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财礼。”
第二种情形:妄冒。妄冒是指婚礼中的冒名顶替等欺骗性行为。《大明律》作如此解释,对女方而言“谓如女有残疾,却令姊妹妄冒相见,后却以残疾女成婚之类。”对男方而言“谓如与亲男定婚,却与义男成婚;又如男有残疾,却令弟兄妄冒相见,后却以残疾男成婚之类”。唐律规定“诸为婚而女家妄冒者,徒一年。男家妄冒,加一等。未成者,依本约己成者,离之。”只对妄冒一方作出刑事处罚,没有对聘礼作出规定。明律对此疏漏补充,女方妄冒“杖八十,追还财礼”;男家妄冒“加一等,不追财礼”。
第三种情形:违律为婚。唐律将违律为婚称之为“依律不许为婚,其有故为之者”,是指法律规定双方不得结婚而违反法律规定结合的情形。违律为婚的情形诸如同姓为婚;杂户、官户与良人之间的通婚。唐律规定违律为婚的婚姻关系不成立,双方需解除婚姻关系。“诸违律为婚,当条称‘离之’、‘正之’者,虽会赦,犹离之、正之。定而未成,亦是。”对聘财的处理则是“娉财不追;女家妄冒者,追还。”只有在女方妄冒为婚的情形下男方才可以追回聘财。如果男方没有过错,娉财仍不得追回,似乎对男方有失公允。鉴于此,明清律在立法上有所改进。明律以男方是否知晓违律为婚判定男方是否可以追回聘财。“财礼,若娶者知情,则追入官;不知者,则追还主。”清代律学大家沈之奇对此解释道:“娶者知情,则必有罪,所谓彼此俱罪之赃也,故追入官。不知情,则被欺骗,犹取与不和之财也,故追还给主。不论已未成婚,皆同。”明清律将过错责任引入违律为婚下聘财的处理,与唐律相比更显公平。
综上可知,古代婚姻法规定中,彩礼是婚约关系存在的证明,更重要的是对婚姻缔结的担保,并且法律一开始对彩礼没有数量和形式的硬性规定,立法者肯定的是聘礼这一古老的婚姻仪式,以此强调婚姻的神圣性和庄严感。但是,由于妇女在传统家族制社会中并不具有独立的个体价值,传统的婚姻缔结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结婚对象的挑选并非基于情感,彩礼中的财产属性被放大,由此导致的女方家待价而沽互相攀比不可避免。最终使婚姻演变为身份、等级、阶层、利益交换的较量。甚至产生最恶劣的后果,家长将女性明码标价视为婚姻市场的交易品,这样的情形从封建社会到民国初年仍然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婚姻法制发生根本性转变,以男女两性个体独立且平等的现代婚姻法制破除“父母之命”的结婚前提,将两性“婚姻自由”视为根本原则,婚姻中的家长意志被剔除。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一条、一千零四十二条继续明确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婚姻自由意味着婚姻的缔结不受任何人干涉,法律更是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传统婚姻中彩礼对婚姻成立的担保价值不复存在,两性婚姻的缔结应当在基于个体独立的基础上,最大地回归其情感价值,而彩礼也亟须回归其仪式感的价值定位。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来源:人民法院报
今天的内容先分享到这儿了,关于本篇【古代婚姻法律,古代女人离婚七出三不进】,是否是您想找的北京法律常识呢?想要了解更多北京法律知识,敬请关注本网站,您的关注是给小编最大的鼓励。
本文地址:[https://www.chuanchengzhongyi.com/kepu/3ed0f3512d3f3182.html]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