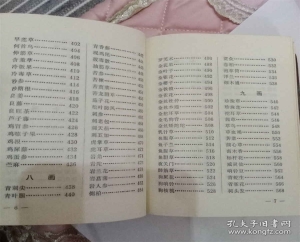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瓦解,新兴国家大幅涌现,每个新兴国家在建立之初都是带着希望而来。但是这些希望由于政权的变化无常和政府效能的低下而趋于破灭。新兴国家军人政权的反复出现导致政治解决冲突的能力不再存在。基于这一背景,近十年来,政治理论界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或国家力量持有浓厚的兴趣。本书也是这一理论和历史背景中的产物。
罗伯特·杰克曼在本书中认为,政治能力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是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他的思路是:要界定政治能力的概念,必须先确定政治的概念是什么。传统的观点一派是把政治看成是统治和控制,另一派是把政治看成是利益分配,而他认为政治是因利益和价值分配引起的冲突,因此在他看来,政治能力就是政府解决冲突的能力,政权用政治手段解决冲突的过程,也就是权力实施与贯彻的过程。政治能力体现在两个维度,或者说,它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制度与合法性。
在制度层次上,政治能力体现为制度的能力,这又具体表现为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国家的实际年龄和实行宪政以来的代际更替年龄。他认为组织生存的可能性会随着组织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已经定型化,组织行为的一般模式得到稳定,个人和组织的角色被固定下来了。因此,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年龄越长的国家,它对环境的调适性也就越强,因而它的生存能力和政治能力也就越强;组织的代际更替年龄越长的国家,它的政治能力也越强。因为,在作者看来,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权威主要是克里斯玛型权威,而这一权威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把自己的权威制度化,但新秩序的制度化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他认为,第一届领袖的顺利继承和继承规则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成功孕育成功的机制下,随着时间的流逝,领袖职位的继承将更可预见,日后的继承过程也将更加惯例化和制度化。因此,代际更替年龄越长的国家,由于这一惯例和制度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在领袖继承问题上会更加稳定。但是,代际更替年龄的前面几年和最初的几次领袖继承的意义是最为重要的。
政治能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合法性。他认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是权力的实施与贯彻。由于权力具有依存性、相关性的特点(relational),因此,人们在关注组织意义上的制度之外,还必须关注政治领袖激发同意和服从的数量和能力。因为权力实施和贯彻是政治能力的核心,因此,合法性又体现在领袖和政权激发同意和服从的能力。因为合法性的反面是积累起来的对政治秩序的挑战,而公民通过非正常渠道来挑战政治秩序表明,他们不相信正常渠道能为他们追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提供一个有效的机制,第二,因为根据理性人的假设,正常渠道外的挑战,意味着他们估计到,他们有机会来获得更高的利益,以抵消非正规政治行为的高成本,而且这种行为说明了,在参与者看来,正常渠道的无效性恰恰表明政权对他们的挑战无能为力,政权也不堪一击。因此他的具体指标是国内冲突的多少。或者说,通过非正常渠道参与政治的程度(主要体现为暴力挑战既存政治秩序的程度)。这样,政权有效地使用政治手段解决冲突(即不需暴力就能解决政治冲突)的能力也就是政治能力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政府越依赖暴力手段来解决冲突,就越会损失自己的合法性,它的政治能力也就越低。
作者集中关注的是政治能力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反对把政治能力的不同要素平均化为一个总体能力的简单指标。因此作者并没有去建立一个政治能力的分析模型,但是,在他的政治能力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建立一个不同的模型。
作者在本书中的逻辑性非常强,但是还存在着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首先,关于政治能力的概念。作者在对政治能力进行定义时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第一,作者认为,对政治能力的任何定义,都必须明确地针对相互关联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行为。但是,通过二分法对政治角色进行这种区分是否合适?如果根据这种区分,就需要首先明确统治者何以能够、依据什么来统治被统治者。可是作者并没有对这一问题给出正面的回答。事实上,根据西方典型的政治理论,都是把政治角色分为代理人和被代理者。代理人的权力基础和来源是被代理人对他们的权力的让渡和授予,没有他们的权力让渡和授予,公职人员的权力就失去了基础。政治冲突不是被统治者不服从统治者,而是被代理人不信任代理人。作者一方面依据这一划分来进行定义,但是另一方面,又没有说明这种划分成立的依据和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第二,作者认为,因为政治的核心是利益和价值的分配以及由之引起的冲突,所以政治能力是政权通过政治手段有效地解决政治冲突的能力。但是,政治的核心是否能等同于政治的全部?不管政治冲突在政治中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但政治冲突涵盖不了政治的一切范畴。借用政治发展理论的分析工具,政治包括政治民主,政治平等,政治自由,政治稳定,政府效能等等各个方面。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有了较高的政治能力,政治民主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可能在一个缺乏民主文化传统的社会里,政府不用解决这一民主问题,并能够通过合法手段来其他的冲突。但是在一个民主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里,民主问题必须解决,但是能够解决政治冲突,就一定能解决政治民主问题吗?尽管因存在民主缺失问题导致的冲突也是政治冲突。虽然作者所谓的政治冲突是因利益和价值分配引发的政治冲突,但是利益、价值这些概念过于复杂抽象,因此政治冲突的概念也容易模糊,指代不清。作者一方面用一个抽象复杂、容易模糊的概念来作为对政治能力进行定义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得出一个关于政治能力的单一性的定义,这也是此书存在的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
在西方的政治学里头,对政治能力的定义其实不少,有人用国家政治绩效来指代政治能力,有人用政治总产值来指代政治能力。其实政治绩效和政治总产值都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如果不能找到一个单一性定义的基础,那么还不如用一个复杂性的定义来取代这一单一性的定义。
其次,作者认为政治能力主要指政权层次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能力。但是,从广义上来看,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既可以指政权的政治能力,还包括社会层次上的政治能力,即特定国家的特定社会的社会政治能力。这一社会能力同样可以通过具体的指标体现出来,比如说,社会的政治觉悟、参与政治的素质等等。毫无疑问,一个具有较高政治觉悟、公民参与政治素质较高的社会,它的政治能力也会较高,对于提高政府的决策水平和政府政策的贯彻实施水平也会大有好处。
再次,从广义上来讲,一个国家的政治能力应该是这一国家的国家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能力应该有个限度 ,这是否意味着作为国家能力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政治能力也应该有个限度?根据典型的国家/社会理论,存在着三个理论派别,它们是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以及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论。以国家为中心,会削弱社会的能力,以社会为中心,又会削弱政府的能力,不利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实施。只有国家和社会关系良性互动,社会能力有限度,国家能力也加以限制,才能谋求社会和国家的良性发展。可是,根据作者的观点来看,由于政治能力是激发同意和服从、通过政治手段有效解决政治冲突的能力,是要延长制度的寿命,是要让权力继承惯例化和制度化,政治能力似乎不应有什么限度。这是一个理论上的悖论。
最后,作者认为,制度年龄(包括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实际年龄和作为政治意义上的领袖代际更替年龄)和合法性一起构成政治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制度年龄为什么能成为度量国家政治能力的一个标准?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实际年龄是被动的、继承的,后人是无法选择的,把它作为衡量具有主观行动能力的一个标准似乎有些牵强。
人们观察、分析政治生活尤其是观察、分析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生活可以有很多的切入点和观察问题的视角。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同一对象,得到的就是该对象的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图景。作为一个分析政治的视角,政治能力这一视角未尝不是一个新颖的视角,但如果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探究事物真理的探路者,我觉得在把政治能力当成一个分析政治的角度的同时,更应该思考是否还有别的更好的分析政治的角度。只有这样,真理才能发现,社会才会前进。这是每一个学人必须面临、义不容辞的任务。
前言序言
在过去的三十至五十年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是一个吸引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关注的兴趣源于两个普遍性的现象。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民主化浪潮使得国际共同体有了一个戏剧性的扩大——也就是说主权国家的数量急剧扩大。而且这一扩张本身激发了人们去理解新兴国家的政治和未来。因此,有些著作也以特别的方式来命名,比如《发展中地区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从帝国到民族国家》(From Empire to Nation)和《旧社会与新国家》(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其中,对新兴国家沿着类似于更多已经建立的国家经历过的历史发展轨迹发展的程度以及这两类国家经历的可能的不同方式,很多学者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
第二,这些学者中有许多人对政治分析的新的行为主义方法也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这一一般性的研究方法的支持者认为传统的政治分析方法,由于它们重视对政治制度的正式特性的描述,而对更多的非正式的观察到的行为模式反应迟钝。与传统分析方法强调特定环境(体制、立法等等)中的特定制度这一唯一内容相反,行为主义者更加重视对建构政治生活的更为一般性的描述的重要意义。
最初对国家政治能力的研究把政治能力置于政治发展的脉络下来进行的。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在政治体系和所谓的它们植根的更为宽广的环境之间划分边界。有些学者寻求界定出所有政治体系都具有的功能,却在对政治文化进行比较的不同的背景中它们又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成功。还有一些人认为种族在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的进程中发挥了作用,或者说,对新的政治体系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与摆脱生存经济相关的变迁)产生了影响。这些研究体现在由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parative Politics Committee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发起的关于政治发展的系列研究著作。亨廷顿的深具影响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1968),在方法上有轻微的不同,他在此书中认为制度化的过程是政治发展的关键要素。
在七十年代,国家政治发展的整个思想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攻击,其中两点最为突出。第一,纯粹主义者(populist)的攻击,他们认为“发展”一词本身就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和目的论的色彩,并由于强调秩序而显得保守。第二,依附/世界体系理论的批评,他们断言,集中关注民族国家显得过于狭隘和容易误导他人。
在最近的十年里,这些批评已经失去了它们绝大多数的进攻力量。相反,民族国家在许多重要的舞台上日益显得重要,而且人们把许多注意力放在国家“力量”的问题上。尽管很少有人承认,但新国家主义——特别是它对国家力量的强调——使得我们回到许多驱动了早期政治发展研究的问题上来。国家力量到底与国家政治能力有关。但是近期研究国家的一些著作并没能清楚地界定“国家”这一概念,并因而使得“国家力量”这一概念也无法界定清楚。一些学者根据公共部门的规模来描述国家力量,但是这一观点很快就陷入了公共部门和私域部门分化(请考虑日本和韩国的例子)的问题当中而难以自拔。另外一些人以更为一般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把国家当作一个“行动者”(actor)。这产生的问题远远超出它所解决的问题。不仅国家(以及国家力量)这一概念依然难以界定,而且,如果把国家当成是一个行动者,这一视角将面临着具体化这一压倒一切的问题。
在它重申了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单位的重要性的意义上,可以说新国家主义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开始。如果我们要在界定民族国家政治能力的问题上有所进展,我们现在最为必要的就是回到基本原理上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有人认为刚刚简要叙述的不同观点的优点最好是通过经验性的研究来加以判定。然而,我相信多数有用的经验研究工作已经完成。在进一步进行经验研究之前,关键是,我们要回到我刚刚提及的理论视角及其引发的经验研究上,并对它们作出评价。我们能从早期的发展研究中,更宽泛地说,从对那些研究的批判中捡拾到什么呢?新国家主义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完善的起点,还是在老调重弹?
本书是由一篇关于国家政治能力(有时代之以政治发展或国家力量)的论文扩展而成的。我在此书中的目的是要探究政治能力的组成要素,并在存在一个可信的国家政治基础之时,来研究我们如何才可能得知和理解。因此本书的主题部分是阐明界定政治能力一般性概念的适当标准。这意味着我首先必须关注概念含义的澄清,而不是关注它的前因后果(当然我会在分析中对后者有所提示)。这也意味着我首先要关注的是理论问题,尽管倒数第二章我分析的是如何度量政治能力的问题。在我对资料进行细致的收集和分析之前,我必须澄清这些理论问题。
第一章考察了在过去三十年里学者们对国家政治能力的研究成果。我从六十年代出现的政治发展研究开始分析,并评估这些研究招致的反应,这包括,总的说来,过去二十年里对国家政治能力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大大地加强我们对那些问题的理解。
在第二章里,我要界定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我认为权力的实施而不是暴力的实施是关键的因素,而且这要求有一个被广泛地认为是合法的制度框架。政治能力因此包括能够解决冲突的合法性制度的建立。我对这一观点和早期的政治发展的观点进行了简要的比较。
在第三章,我要根据第二章中的讨论来考察近期关于国家的著作对政治能力的研究有何启示。这些著作可以分为两种一般性的观点:有些人强调公共部门的规模是国家力量关键的要素,另有一些人更为松散地探讨国家“自治”。我认为这些观点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多大作用,尤其是有两个问题极为突出。第一,我们很难在公共部门和私域部门之间作出区分。第二,国家自治的讨论典型地模凌两可,并且深深陷于具体化的问题之中。鉴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寻求一个研究国家政治能力问题的新的视角就显得非常必要。
我所认为的制度是政治能力的关键和中心的观点只是一个一般性的观点。在第四章中,我着重于界定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制度的特定组成部分。根据对始自马克斯·韦伯强调更新倾向的分析研究,我认为与组织年龄紧密相连的惯例化是政治能力的关键的要素,而且组织年龄也需要根据实际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的标准来加以考察。组织年龄的三个要素是独立的,它们是: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年龄,最近实行宪政秩序的年龄以及在宪政秩序中最高领袖继承发生的次数。
政治能力的另一个要素是合法性。制度年龄影响政治能力,凭自己的地位,合法性也应得到研究。这个问题会在第五章得到解决。根据在第二章中对权力和暴力的区分,我认为,在不公开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就能解决问题和冲突的意义上,制度或政权就是合法的。但是合法性是一条“双行道”,我们需要关注被统治者表现的同意和服从的程度。相应地,我也认为合法性是一个表现对政治秩序的非正规的或暴力的挑战的反函数。
在第六章,我集中探讨如何度量根据制度年龄和合法性标准来界定的国家政治能力。在这里,我把一般性的定义和具体的操作指标连接在一起。当然,政治能力的测量必定不精确,但度量标准的确定也可以减少定义的模糊性,尽管如此,它却很难完全消除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第六章中采用的数据影响到数值的次序,并可以用来对政治能力进行民族国家间的广泛的比较。
最后一章我要探讨这些研究对未来的经验性研究工作的启示,并把我的视角和其他学者的角度进行比较。我贯穿本书的目的是要提供一个关于国家政治能力研究的新的概要。
有很多学者阅读了全部或大部手稿,并作出了回应。我要感谢加布里埃·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肯尼思·A·伯伦(Bollen, Kenneth A.,),米凯尔·布雷顿(Michael Bratton), 布鲁斯·布伊诺·梅斯裘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 玛丽·杰克曼(Mary Jackman), 莱特歇·洛森(Letitia Lawson), 阿仑特·利日法特(Arend Lijphart), 西蒙·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特里·默伊(Terry Moe), 肯尼思·奥甘斯基(Kenneth Organsk), 布莱恩·思尔沃(Brian Silver), 兰多夫·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他们对我的手稿给予了非常有益的批评和评论。尽管我没有完全采纳他们的建议,但是本书由于他们的建议而要好得多。米凯尔·布雷顿也将我从一个令人烦恼的章节中解脱出来,而布鲁斯·布伊诺·梅斯裘塔却将我引领进著名的斯普勒工会(Labors of Bertold Spuler)。玛丽·杰克曼近期著作《父权主义和冲突》(Paternalism and Conflict,1993 )一书的读者将会认识到我已经欠了她知识上的债务,尽管我们有不同的经验关注焦点。朗·罗杰罗(Ron Roggiero)在查找资料上的帮助是无价的。在过去几年,我与很多学者讨论过此书的不同部分。尽管在“国家新闻”(State News)上能发现一些令人欣慰的东西,但大多数并不如此。此书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的和集体性的回应才有相当的完善和提高。
在斯坦福行为主义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 at Stanford)的伙伴的帮助下,在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支持下,我完成了我的初稿。正如许多人发现的一样,我发现这个高级研究中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跨学科环境,它的作用在文中只现一斑。我要特别感谢玛格丽特·阿玛拉和罗森·托尔(Margatet Amara and Rosanne Torre)在提供书目上的额外的帮助,还要感谢弗朗西斯·杜伊格南(Frances Duignan)在确保所有关键事情得以运作上提供的帮助。我还要感谢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系和政府事务研究会(Institute for Governmental Affairs)、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学术委员会(Academic Senate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给予的关键性的支持。拉凯尔(Rachael)和索尔·杰克曼(Saul Jackman)明智地保留住对自己的冷静(表现得好象他们已经有了另一选择),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诸如约罗县防止虐待动物协会(Yolo County SPCA)和英式足球上。不管别人是否会认为因为他们的努力而使本书显得更加完善,但他们的努力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
由于他们的帮助,我才产下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鸭蛋”,但这只是证明了我作为一个“丑小鸭”的缺陷和无能。
第一部分 政治能力研究的背景第1节 早期的发展文献(1)
我们生活中所见所想的大多数变化都应归因于我们赞成或反对的思想。
--罗伯特·福罗斯特,《黑房子》 “The Black Cottage”
直至50年代早期,比较政治研究都局限于非常狭隘的外国政府的研究。比较研究至少在以下两重要方面受到限制。其一,比较研究起初只是框架性的(configurative )研究,把研究的重点仅放在正式的制度安排(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和政治制度史(political institutions ),满怀希望能藉此说明特定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其次,研究对象也仅局限于一小部分国家。典型的现象常是,一篇关于比较政府的论文事实上只是撷取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二战后的苏联政府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描述。
这两大局限导致了一大批强调个案研究重要性和否定从案例中得出结论这一做法的文献。比较政府研究隐含的意图不是要对政治现象作出比较或总结(下结论),而是要获得一些对西欧一些国家政治现象的感性认识,至少,这样一种认识会有助于孕育出对美国政治现象原貌的更为广泛的理解。但个案研究强调的是全国性的差异(cross-country),而不是其相似性,也不是简单相加而成的类似于知识集合体的任何东西(Eckstein ,1963),实际上,那不是它们的目标。
然而,在最近的三十年里,这些情况大多已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二战后非殖民化进程和与之相伴生的“第三世界”的兴起。即使很难说印度次大陆是第一块获得独立的地区(一般认为是拉丁美洲首先获得独立),但由于下列两个原因印巴分治及其非殖民化因而显得最具影响。首先,大英帝国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一直是最大的殖民帝国。其次,印度被认为是英国殖民体系上最大的一颗明珠。印度的独立为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最终解体和其他帝国殖民体系的瓦解提供了动力(Smith,1978;Fieldhouse ,1982; Low,1982)。
非殖民化进程贯穿了整个五十年代,而1960年宣布民主独立的国家的数量是空前绝后的。人们容易忘记,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的时候仅有五十一个会员国。可是从那年起,联合国成员国的数目猛增至150个。而且第三世界国家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这个变化在今天使得人们认为殖民统治不具合法性。民族主义在今天-不管好坏-成了支配性的意识形态(Gellner,1983)。联合国宪章也把民族自决权列为最主要的权利。
民族自决权是二十世纪特有的权利,理解这点至关重要,同样,认识到民主观念在帮助赋予民族主义合法性和削弱殖民统治的作用也至关重要。对殖民统治的最大不满是殖民统治者既不来自也不代表被它统治的人民(Emerson ,1960,243)。因此,削弱宗主国合法性的一个途径便是提高建构民主制度的呼声。建构民主制度也就成了用它来赋予自己作为本国居民代表的合法性的殖民地精英的一个力量源泉(Emerson,1960,242-243;Young ,1976,Chap.3;Collier,1982,32-33)。结果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要求独立的殖民地精英在他们成功之前不信奉民族自治和民主政体的一致性(Shils ,1964,103)。
非殖民化明显带来一些问题。由于没有明确主权如何以和平的方式移交给独立的民族自治政府(事实上只有少数几个殖民地和平地获得独立),帝国权力在1945年后仍给人一个在殖民地平静的存续的印象。欧洲人认为,如果必须离开,那么,用(麦肯齐)Mackenzie的话说,就是“必须体面地离开,体面则根据欧洲人的标准被定义为在殖民地必须建立良好的政府和民主制度”(1960,465)。
对于新兴国家来讲,主权该转让给谁并不总是明确的,当然,在有些情况下,这在民族运动和民族组织中已经得到明确,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并非如此。即使在民族主义组织中已经界定,但政治参与者对何种权力转让给谁的问题并不总有自信。哪个民族运动最具代表性?谁的民族运动?民族边界应该划定在哪?印巴分治是最经典的例子,正如随后一一发生的事件表明的,甚至分立也并非永恒。
如果非殖民化给殖民帝国和殖民地带来了问题,那它也给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带来了研究的空白点。比较政治学领域最初关注主要欧洲国家(老牌国家)的特点使得它对新兴民族国家出现的反应措手不及。然而,比较政治学家要赶上形势并不需要走很长的路。尽管在五十年代对政治发展的分析几乎为零,但到六十年代初期这方面的文献就非常丰富了。确实,六十年代非殖民化进程达到顶峰,六十年代也代表了几大学术研究领域发展的顶峰。
最为著名的是,1960年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 )和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的出版。这本论文集提出了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成为数年后由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发起的政治发展系列研究的基础. 阿氏和他的伙伴们对民族国家政治体系政治能力的问题和政治进程怎样与外在更广的社会经济环境隔离给予了足够的学术关注。
他们用输入、输出功能范畴来标示各政治体系的共同特性。他们把输入功能分为四类: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录用、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治交流。在输出或能力方面,他们强调政治决策、政策实施、政治裁决。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及其同事并不认为在实现其功能时各政治体系同等有效,但他们认为成功的实现各项功能是政治发展的关键。
同年,西蒙·马丁·利普塞特(Semour Martin Lipsets)出版了《政治人》(Political Man)一书。作为其对政治社会化领域研究的一部分,他对维系稳定的民主制的因素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尽管其中有一部分分析是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个欧洲民主政体的崩溃,他还是从拉美经验中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同步进行是稳定民主的一个重要前提。利普塞特进一步提到经济发展的时机和民主进程的步调 是民主制度得以成功的关键。
在1960年拉普特·爱默森(Rupert Emerson)出版了《从殖民帝国到民族国家》(From Empire to Nation)一书,这是一本研究亚洲、非洲非殖民化进程和主权从殖民帝国转到地方精英手中的专著。他追述了西方向外扩张并最终因它而削弱殖民扩张的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横贯全世界的扩散史。他还谈到了非殖民化进程对前殖民地随后政治发展模式的影响。
在随后的几年里,有关政治发展的文献迅猛增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61年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社会流动与政治发展》(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论文的发表,他在此文中分析了伴随着工业化的社会变迁与政治制度的生命力、社会变迁与度量社会变迁的各项系统性的经验指标之间的关系。克利福特·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在1963年发表了同等重要的论文《整合革命:新兴国家的原始情感和公民政治》(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据称为是对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最大影响的问题上:民族国家情结及与之相抗衡的宗教、种族、语言、地区情结的整合。
第一部分 政治能力研究的背景第2节 早期的发展文献(2)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亨廷顿(Sameul Huntington)在1968年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书中提出了“到底什么是政治发展”的问题,并回答说:政治发展就是高效的、能确保秩序和稳定的政治制度的创建,简单的说就是政治制度化(1968,VII)。早期的一些文献把政治发展等同于民主制度的建构和发展,这被很多批评家认为是种族中心主义 的体现。更公正的说,正如我早已表明的,作为非殖民化运动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据就是民主思想。为了避免这种简单的等同,亨廷顿努力寻求一个关于政治发展的一般模式:“国家之间的最重要的差别不是它们的政府形式,而是政府制度化的水平”(1968,1)。 因而亨廷顿过分强调秩序和稳定。
亨廷顿的创造性分析源自他对政治制度的细心关注。早期学者在宽泛的社会变迁与政治发展的边界上模糊不清,亨廷顿却对此非常清楚。他把政治制度化界定为四个组成部分:调适能力,复杂性,自主性,内聚力。套用这个公式,发展就只是一个度的问题,政治制度的调适能力、自主性、复杂性和内聚力的程度越高,该制度的能力也就越强。拥有制度能力相对较强的国家,它的政府的层次也就相对较高。
制度化这个概念内涵丰富,确实,人们普遍认为亨廷顿的书对政治发展的问题进行了一次最为彻底的清扫。无论是在对政治事件的平常的议论还是学术争论中,政治真空的概念一直得以使用(e.g., Zolberg 1966,chap.1)。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时期,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在欧洲势力撤退后,将给当地留下一个没有清晰边界的政治权威的真空。或许关于这一问题最为著名的论述是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和1947年的演说。他说,工党政府由于印度次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而迅猛发展。他断言在当地没有可以接受权力转让的代表性组织,权力撤退的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混乱和屠杀。 最近,我们目睹了黎巴嫩自1975年内战爆发后的一些事件。我们不幸地看到1975年以后黎巴嫩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政府能控制整个国家,反之,不同的党派、组织、势力控制着国家的不同部门,并在军事上相互竞争、抗衡。在国家的层次上,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派系或派系联盟具有打败对手的实力从而留下了政治真空,这就是内战的实质。这种惨剧在北爱尔兰继续上演着。毫无疑问,新教徒势力由于有英国的军事支持而比其它派系或比黎巴嫩的各个势力更有能力实现对国家的控制,但控制远未实现。在爱尔兰遗留的政治真空比黎巴嫩要少,然而政治制度受到自身力量的强烈限制。北爱尔兰的中央权威缺乏解决问题的政治途径,政府机构脆弱不堪也就势所必然。
最近,我们经历了前苏联及其东欧保护国的崩溃。新成立的十五个国家的政治生命力值得怀疑,源于种族权利要求的内战也就很有可能伴随着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政治分裂而爆发。通过对这一问题(为民众广泛认可的政治权威的缺失)的关注,制度的脆弱性问题得到了强调。
因为对这一问题有着清楚的关注,亨廷顿的分析也就显得更趋重要。它提醒我们政治能力的衰弱不只是一个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简单问题。黎巴嫩居民的文化素质在中东国家中最高,在1975年前,贝鲁特还是一个商业和金融中心。确实,在1975年之前,黎巴嫩还被普遍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有可能实现民主的国家。与此相似,与世界范围内的其它经济模式相比,北爱尔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这些例子清楚的表明社会的现代化不一定就会带来政治的发展。
亨廷顿的分析模式还告诉我们,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政治衰朽(political decay)可能发生,制度也可能崩溃。换言之,不象某些更为乐观的现代化研究学者所说的那样,政治发展不是伴随着工业化的社会变迁的自然结局。与此同时,政治衰朽的可能发生意味着发展不是一个畅通无阻、直线前进的过程。
但是,亨廷顿的观点还有更深层的意义。他认为,工业化、非殖民化以及其它的发展进程带来了没有预料到的、与维持秩序相冲突的大众参与政治的要求。如果要在广泛的、非组织性的大众政治参与活动和有限的、而又是有组织的大众政治参与活动中作出选择的话,亨廷顿倾向于第二种选择,因为在他看来,秩序最终是更为重要的追求目标。在政治真空中由于缺乏组织性和连续性,参与必将导致混乱。因此,在政治结构脆弱的国家里,不应该鼓励大众参与。
亨廷顿用一个等式来表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是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的比率(1968,55)。不稳定不只因政治容量(political capacity)的低弱而产生。 确实,假如大众参与不足,即使制度化的水平低下,同样可以维持政治稳定。只要参与的水平和政治容纳能力保持一致,政治动荡就不太可能,亨廷顿把这种情况(参与的水平低于容纳水平)称为公民政体(civic polities)。
问题是假如参与水平超出了容纳能力,比如说在执政官政体(praetorian polities) 中该怎么办。其实这才是亨廷顿真正关心的问题:
要想以这些国家的政府形式来给它们分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无庸置疑,美国是立宪民主制国家,苏联则是共产党专政的国家。但是,印尼、多米尼加、南越、缅甸、尼日利亚、厄瓜多尔、叙利亚等国家实行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它们也进行选举,但它们的民主显然不是丹麦和新西兰实行的那种民主。它们有专制统治者,但又没有共产党国家那样高效的专政。唯一人之命是从、依赖个人魅力的领导者或军事独裁者都曾大权在握。把这些国家列入任何一类政府形式都行不通,因为捉摸不定、集各种政体的脆弱性于一身是它们独具的特征。具有非凡魅力的派系首领、军人政权、议会政权、深得民心的独裁者,你方唱罢我登场,眼花缭乱,无法预料。政治参与既不稳定,也无规则,在这种政体和那种政体之间来回摆动……这种动荡是缺乏政治共同体和政治参与超出政治制度化限度的明显标志。
这种动荡不安正是政治发展缺少现实基础的外在表现。
尽管亨廷顿比他的前辈们对政治结构明显给予了更多关注,但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对此问题有过总体的论述。例如多伊奇就曾说过,在政治能力匮乏的国家,社会流动可能导致不稳定,因而社会流动的步子要适中。奥而森(Olson)在1963年有过近似的论述,他说,迅速增长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和经济的混乱,而这又加剧不平等并最终引发政治动荡(Olson,1963)。根据这类论述(Geertz,1963;Almond,Powell,1966),可以说,过快的增长不一定会带来政治能力的同步、协调增长,期望的增长超出了整合和满足这些期望的制度能力的范围。
在有了这么多的学术回顾之后,加上过去三十年来大多数非洲国家糟糕的经济状况,有人或许要问为什么要对快速增长和大众参与的问题给予这么多关注。问题就在这些学者对新旧国家进行对比后发现,老牌国家或平坦或曲折的政治发展都花了几百年的时间。它们的政治发展道路并不完全一样,但在大众政治参与的要求产生之前,它们的领土已经通过军事征服或其余手段得到固定,制度已经形成并日趋完备。此外,新兴国家必须面对一个与老牌国家形成完全不一样的国际背景。
人们不要忘记民族国家的现代形态起源于欧洲(Bull,1979;Badie, Birnbaum,1983;Gellner,1983;Hobsbawm,1990)。一些人把现代民族国家看作是已经消失的欧洲势力在当地留下的遗产 (Bull,Watson ,1984,2)。尽管安德森(Anderson)已把民族感情的起源追溯到十八世纪移居美国的欧洲移民的后代(Creoles) (1991,chap.4),然而,艾利·克杜尔(Elie Kedourie)却进一步声称民族主义患的是欧洲病(“The European Disease”,这一术语引自 Geertz, 1977,249)。当代国际体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的欧洲,作为现代国家,新兴国家要比英国少两百多年的历史,比德国和意大利要少一百多年 。许多欧洲国家(nation)的历史甚至比亚、非、拉的新兴国家的历史更短 (Connor,1990)。 国家权利平等和主权平等的原则确立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这一原则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的建构后得到遵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的成立时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述(Bull和Watson,1984)。成年人都应享有公民权利的原则与国家主权原则的并行则是非常晚近的事(Bendix,1978)。
因此,人们对新兴国家的经历与老牌国家的截然不同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更明显的是,新兴国家同时经历了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nation and state building)、巩固政治制度、满足广泛的政治参与的要求的过程。用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话来说就是,“新兴国家今天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它们必须面对累积的革命要求。人们要求参与、要求国家民族的统一、经济状况的好转、法治和秩序,并立即、同时予以解决。”(1966,39;还可参Rustow,1967,227-33;Linz,1978,7)。正如我早已提到的,创造了新兴国家的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建构在源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强调代表制的民主理念的基础上。对代表制的强调本身引发了大众参与的要求并使它日趋高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现代化早发国家的历史并不能为新兴国家提供一个清晰的蓝图,政治参与的问题就只是新兴国家的特殊问题, 因而要关注政治参与,要强调政治秩序。
第一部分 政治能力研究的背景第3节 对发展研究的批评
在七十年代,整个发展的思想遭到两个方面的攻击。首先是我们姑且把它叫作纯粹主义者(Populist)的批评,他们声称,正是政治发展这一名词本身把一些毫无根据的、带有目的论色彩的东西带入分析当中,发展概念的使用必定表明发展论者在先念中预设了一个目标,这一目标就是西方的制度。引用批评家的话说,就是“由于西方政治、文化霸权作怪,种族中心主义已经甚嚣尘上,仿佛只有西方的政治发展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模式”(Kesselman ,1973,153)。用这种观点去衡量发展思想,它只不过是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魏雅达(Wiarda)接下来认为我们必须对发展或现代化这类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进行再认识,比喻在定义、概括或对现实进行描述时非常重要,但不应把它误认为是现实本身。比喻方法在对现实进行描述时不仅有着各种局限,而且这些比喻是西方的,与非西方世界既相关又不相关(更多情况是属于后者)(Wiarda,1981;Janos,1986,65-66;Somjee,1982,chap.1)。
与此一道,还有人反对在发展研究中对政治秩序的过分强调。正如我早就提到的,政治秩序是亨廷顿进行分析的核心概念,对其他许多研究政治发展的人来讲也是如此(e.g.,Zolberg,1966)。反对意见认为政治秩序并不一定是需要予以重视的唯一价值。专制统治也可能维持“秩序”,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站在专制统治的一边?难道那些竭尽全力消除暴政的人也是在制造混乱吗?在亨廷顿看来,真正无序的是暴力政体(执政官政体),对其它的一些东西,他却加以回避。没有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大众参与只会产生过度参与的政治危机。确实,亨廷顿进一步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
通过考察是否存在能够满足大众利益的政治制度,我们可以对发达社会和不发达社会进行政治上的区分。我们还可以借助它来区分道德社会和非道德社会。制度化水平低的政府不仅是脆弱的政府,还是坏政府。一个缺少权威的脆弱的政府,既是一个无法实现自己使命的无能的政府,还是一个官僚贪污成风、军队胆小怕事、教师愚昧无知的道德败坏的政府(1968,28;斜体为原文所加)。
批评家们发现对秩序的重视和把秩序与道德连在一起成了一个势不可挡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既然权力地位的维持是它们的必要条件,那么采纳这种关于权威的观点就是在骨子里头存在着天生的偏见。”(Hopkins,1972,275-76)。另外一位学者说道“秩序是上层强加给大众的,这样大众就是政府政策可以随意操纵的对象……对政治秩序的绝对重视导致了对过去同样得到重视的一些对象,比如经济发展、社会改革、当然还包括政治民主化的轻视和再思考。”(O’Brien,1972,363,365)。考虑到美国越南外交政策的明显失败,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问题(Smith,1985,543)。
对发展研究的第二个攻击来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依附/世界体系理论学派。批评主要集中体现在这一主张上:民族国家并非彼此是分离的,而是置身于一个更为宽广的系统中。这是一个强国家的统治阶级剥削弱小的、依附国家的世界体系(Baran,1957;Furtado,1964;Frank,1969,学术会议的发言。)。按照依附理论的这种说法,发展研究正因为假定发展是一个由内部力量支配的过程而误入歧途,认为更具现实意义的做法是去证明强国的精英用什么方法造成了依附国家的不发达。外国资本对穷国的经济运行具有潜在的不良影响,象跨国公司那样的外国机构也可能会破坏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这是依附理论千方百计要加以改变的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在对后独立非洲进行研究时,与新殖民主义分析视角类似的观点多得惊人——它们都含蓄地主张非殖民化运动与其说是真正的成功,还不如说是表面上的成功。
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a,1974b)的世界体系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非常重视,在这一体系当中,中心国家(强国)剥削边缘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一布局中,有一部分国家居于矛盾的、模棱两可的位置,这就是半边缘国家(e.g.Chirot,1977)。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世界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整合的、统一的体系。沃勒斯坦认为世界经济自身就是一个基本的分析单位或“对比分析的实体”(1974b),当今的政治模式只能放在源于十六世纪的这一体系中去理解。
按这一角度去考虑,民族国家的自主就没有分析的空间。事实上,世界经济是基本的分析单位并不含有这种意思。它只是认为由于这一视角的局限性或者不相关性,使得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的研究误入歧途。民族国家只是一个局部层次上的统一体或非系统的东西(Wallerstein,1974b)。它的政治机构甚至从潜在的意义上都没有自主性。比如说,在一个“中心国家的统治集团与边缘国家的统治集团借助一种可怕的方式互相紧密联系的”世界中就是如此。因此,七十年代中期沃勒斯坦(1976)宣告整个“现代化”理论的死亡完全恰当,这丝毫也不令人觉得奇怪。
最近十年内,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清醒过来的人日渐增多。首先,有些人认为沃勒斯坦对十六世纪以来欧洲历史的解释具有根本性的缺陷(e.g., Skocpol; Gourevitch,1978; Smith,1979; Zolberg, 1981; O’Brien,1982)。奇洛特(Chirot)则走得更远,他认为用韦伯的观点来解释西方的兴起要更为准确。 与此同时,我们很难从依附/世界体系理论中找到有关能够解释在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当代世界中,民族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不平等的令人信服的系统的证据(Philip,1990)。比如说,跨国公司的投资并没有阻碍第三世界的经济增长(Jackman,1982;Firebaugh,1992)。一些有效的证据也并不足以证明处于世界经济非中心地位的相关国家就会加剧国内经济的不平等(Bollen ,Jackman,1985)。
其次,在依附/世界体系理论学派里,开始有人认为民族国家至少在有些地方可以灵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有些学者已开始重视依附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可能性。按这一观点,有些国家,尤其是那些半边缘国家,能够取得相当可观的经济发展(e.g.,Cardoso和Faletto,1978;Evans,1979;Haggard,1990)。依附发展的主张仍然重视国外资本和跨国公司的作用,但可以通过制度及其实施者来对它的作用进行修正和调整。他们甚至认为中心地带以外的国家可以取得真正的经济增长。
也有人并不认为依附发展理论对世界体系理论有很大的修正。例如,史密斯就认为对当地因素、国家角色和真正的经济增长的意义的认识并没有拒斥依附理论方法的必要。他反而这样认为:依附理论的著作并非头脑简单的表现,相反,去学习它的那些使它自己能够产生不同学术派别并能使自己及时改变观点的分析概念,就一点也不奇怪……象其他连贯的理论思想一样,依附理论也有保护自己免受威胁和保持自己学说完整性的阀门(Smith,1985,555-5,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然而,我们并不真正需要学习它的什么东西,最初的依附/世界体系理论吸引人的是它的连贯性及一致性。一旦我们接受上述三大修正,整个理论将因失去它的一致性而变得折中和无所适从。确实,接受这三大修正,意味着整个依附理论将要失去它的理论上的特殊性。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把这一学说当成意识形态或教条来进行辩护的话,那么它代表的只会是“本末倒置”(Almond,1987,117-47;Packenham,1992),它的有效性也只有通过诉诸神学的标准而非世俗标准来加以判断。这也是社会科学家应该高兴地给自己开脱的一项任务。
国家的作用可能变得日趋重要的观点正在成为最新的正统思想 (请参Krasner,1984;Benjamin,Elkin,1985;Evans,Rueschemeyer,Skocpol,1985;Nordlinger,1987)。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是强国家 ,当然,只要它是一个强国家,学者们就认为甚至在一个由超级大国和跨国公司主宰的世界中,政府在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中仍然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尽管在过去的十年里又有了对国家力量(state strength)进行研究的兴趣,可对这一概念仍然没有界定清楚。强国家被说成是更能够对环境进行控制的国家。在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国家确实比弱国家更有力量。国家力量(strength)与政治容量(capacity)或政治能力(capability)密切相关的观点,也就是说,当前对国家(states)的理论关怀事实上反映了对推动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研究的课题的再度重视。
除此以外,在国家到底由什么构成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混乱。一些人认为它包含官僚机构,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包括政治人物(政府首脑和他们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人把国家等同于制度甚至国家层次上的政策(我将在第三章中讨论这一问题)。国家概念的这些差异使人回忆起早些时候区别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政体(regime)和权威(authority)的种种尝试(Easton,1965)。通过以上的对照分析,使我们认识到由于政治发展研究的经验参考价值的模糊性,使得对它的研究难以为继。我相信最近对“国家”这一概念内涵界分的尝试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遭到同样的命运。
第一部分 政治能力研究的背景第4节 对发展批评的再思考
我们又应怎样去理解过去三十多年的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研究的理论流变呢?对这一问题的一般解释是六十年代遍及整个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信心在七十年代已经消失,而到七十年代末,发展研究处于一个危急状态(e.g.,Hermassi,1978;Smith ,1985)。另有一些人认为六十年代对发展的研究是第一代,依附理论则是这一研究的第二代,试图超越早期争论、对国家的最新重视的发展研究则是第三代(e.g.,Kohli,1986)。换言之,有很多人认为,六十年代发展研究的一般分析框架已经完全为一个新的理论取向所取代。正如克拉斯勒(Krasner,1984,226)所指出的:
暂且不管新的国家取向的研究之间有何不同,但这些研究确实给曾经支配美国政治科学的研究传统提出了挑战。它们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空间,回答的是全新的问题,调查的是全新的经验现象,提供的是一些全新的答案。
库恩(Kuhn,1962)认为规范的科学(normal science)研究是在特定理论范式(paradigm)的背景中进行的,范式就是界定关键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现象可以引用库恩这一观点来解释。当流行的规范科学的理论范式难以解释新现象时,科学也就充满危机。结果就是主流理论范式的转变。 有人把库恩的思想应用到政治发展的研究上,并认为六十年代的理论范式到了七十年代就站不住脚了。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一次显著的范式转变发生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斯戈普(Skocpol,1985,8)写道,“一场发生在宏观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转变正在进行,它包括对在经济和社会中国家的作用的重新思考”(另外请参Chilcote,1981;Krasner,1984;Janos,1986)。
然而,对二战后政治发展研究的简要回顾让我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那就是我们的研究兜了一个圈子。尽管很少有人承认,当前对国家的研究与六十年代对政治发展的早期研究有着许多共同点(Binder,1986有相近的结论)。特别是国家中心(state-centered)而非社会中心(society-centered)的观点与亨廷顿对政治制度自主性的强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国家主义(statist)的支持者认为旧有的发展研究完全忽视了国家的作用并且把这归因于本质上属于行为主义(behavioral)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政治研究的方法(e.g.,Krasner,1984;Skocpol,1985)。然而,只要我们带着问题去阅读发展文献就会发现这些研究并不同意这一观点。这些研究的主要学者例如爱默森(Emerson,1960)、吉尔茨(Geertz,1963)、派伊(Pye,1966,chap.1)非常清楚的关注国家这一问题。亨廷顿对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的集中关注也含蓄地表明他对国家的集中关注。认为这种发展研究沦为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牺牲品的观点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象政治能力(political capacity)、社会流动和种族差异等概念所指的是社会和民族国家而非个人的特征。
对上面观点的明确的反驳是,历史分析忽略了新的国家取向研究提出新问题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在早期的研究中就遭到了忽视。然而,就这一点,史料并没有明确的记载。首先,早期界定政治发展概念的尝试遇到的困难与更晚近的研究遇到的困难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已普遍使用国家力量(strength)一词,但仍需对它予以界定和说明。确实,从研究国家由何构成这一课题迄今的十年里,它的含义一直没有得到明确。比如,著名的论文集《把国家带回》(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就没有对这一问题予以足够的关注。唯一给国家概念做出明确定义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国家是一套被授予权威,以制定对居于特定领土内的人民和组织具有约束力的政策并加以实施(如有必要,就使用暴力)的组织体系(Rueschemeyer , Evans ,1985,46-47)。霍尔和伊肯伯利((Hall,Ikenberry,1989,1-2)提出了相同的看法。确实,韦伯的定义提供了一个起点,然而,他留下了几个没有解决的关键问题。对始于韦伯国家定义的早期发展研究的回顾是非常有用的(e.g., Almond, Coleman, 1960, 5)。
其次,试图界定国家含义的那些著作很少包容新的内容。埃文斯(Evans,1979)对巴西的依附发展有声名卓著的分析,他特别关注国家的作用。尽管埃文斯没有明确界定国家这一概念,但他指的国家看来似乎是指国家的政治能力(capacity)。
国家机器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政府必须控制其它的机构和组织,以便对自己的行动提供刺激和支持。最后,知识、技术和对信息的控制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79,44)。
这看起来与亨廷顿关于政治制度化的标准完全一致,尽管后者在任何地方都无法举例。亨廷顿把一个强大的政治机器看成是保持秩序和控制的手段。埃文斯则把它当成产生有效控制和进行积累的工具。
有趣的是我们有了一个关于“现代国家”的更为准确的定义。按照芬纳(Finer,1975,85-86)的观点,当代的民族国家有以下几个特征:
承认公共最高政府机构的特定领土范围内的居民人口;
这一政府由执行决策的公共服务和军事服务机构所推动;
拥有主权国家的地位;
有一个建构在共同国籍的自我认识上的对共同体的情感;
在其成员共同承担责任、义务、并共同享受社会公共服务
的意义上,该国的居民构成一个共同体;
芬纳的定义比近期的一些论述更为具体、明确。即便如此,他的界定与早期对发展的定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确实兜了一个圈子。这一结果使得伊斯顿(Easton)下结论说,近期对国家的关注已演变成概念界定的狂热,这种狂热给了人们一种并没多大必要的研究的合法性和归属感(in-ness)(1981,306)。
如果说我们从六十年代直到现在兜了一圈后又回到了起点的话,那么再回到五十年代的分析传统中,我们等于兜了一个更大的圈子。我在开头早已提到,六十年代后的政治发展研究是对被自身取代的结构主义方法的一种回应,在结构主义避免一般化的地方,我们却鼓励政治发展研究去一般化(generalization)。
在过去的大约十五年的时间里,历史主义(historicism)得到复兴。每个国家看起来似乎都有着一个特定时期特定产物的唯一的政治经历。比如,瓦仑求拉(Valenzuela)就说:
依附理论最初是一个并没有声称自己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历史主义分析模式。这是依附理论并不关注精确的理论建构的原因,这种现象在现代化理论中也存在。依附理论更多的是关注历史分析框架生来就有的特定历史阶段(1978,546)。
这一论述与《评论》(Review)杂志有相同的倾向。它们都认为历史在跨越时空的经济分析中、在空洞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在理论学说的转变中都居于首要地位。 可是,它们实际关注的东西多少有点不同,埃文斯、路斯彻米尔(Rueschemeyer)、斯戈普都强调自己希望国家力量……的问题可以仅通过辨证思考国家与社会间的非零和博弈及复杂的互动来引起讨论(1985,355)。在赞成他的归纳是采用历史主义的归纳法后,奇尔科特(Chilcote)进一步论述说:
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许多不同的见解。从一个时代、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时代、文化,观察世界的角度都有不同。真理只是相对于观察者所属的特定时代和文化来说才为真理,真理只是暂时的、相对的,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真理。(1981,69)
最近,拉金(Ragin)主张我们放弃变量取向(variable-oriented)的比较研究方法,而代之以强调在个案中不同的特征和原因都适合的案例取向(case-oriented)的研究方法(Ragin,1992,5)。他们声称案例取向方法的优势在于估量事物的复杂性这一目标要优于获取对事物一般性的认识这一目标。与其选择关于现象所属类型的更为宽泛的或然性观点不如选择关于现象所属类型的更为狭窄的必然性观点(Ragin,1987,54)。强调复杂性、归纳法优越论(inductivism)、决定论和相对主义的论述看来很难得出一个有效的经验的一般性结论,或者说这些论述甚至很难与一般性的结论和谐共存(Gellner,1985;Kiser,Hechter,1991;Liberson,1991)。 三十年前,爱克斯坦(Eckstein,1963)极力主张简化(simplification)比较政治的研究,今天,他的这一观点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
如果说历史主义有新的保守倾向的问题,那么我曾多次提到的后来的范式转变也有同样的问题。确切地说,在国家力量这一话题(曾经是政治发展的话题)的范围内,发生了一场话语的革命。但这并不表明研究的时尚也已发生转变,它只是一次话语的革命,而非实质性的革命。象早期的文献一样,当今的研究也从韦伯的思想中汲取灵感,但并不等于这些研究已让我们离概念界定问题的解决更近一些。不管他们是如何声称早期的研究如何具有精确性和科学性,这些研究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们的许多理论建构(比如输出功能和机构的自主性)用的是在现实中并不清晰的抽象的话语来加以表述的。
当我们对盛行于二战后的政治科学中的自负的抽象理论和夸夸其谈的发展理论加以整理时,我们其实是在对它进行净化(Tilly,1986,116),我们并且会发现,说近期的研究代表了一个范式的转变其实有点夸大其辞。这种转变假定了一套能解释这种经验现象而不能解释另外的经验现象的理论的实际存在。考虑到许多关键概念令人难以捉摸的特点,在早期的发展研究里,理论与经验事实的联系常是松散的。然而记住这些研究正在另一生疏领域规划新的研究方向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对得出一般性结论确实进行了严肃的尝试。最近的文献最令人吃惊的是它的关键概念(最显著的是国家概念)的模糊性。把它与对历史主义的抛弃相联系,我们不难发现,从这些模糊的概念里头产生出有用的研究纲要的前景并不明朗。发展研究的各种方法和独立于各种需要加以考虑的经验现象之外的意识形态潮流一同兴衰。正如盖德兹(Geddes)最近指出的,
当一个学说产生了看似很有道理的偏见时,学者们感到没有必要去惹麻烦,再没必要去挖掘足以证明它的材料,因此,也就无法找到足以推翻它的证据。由于缺乏用来精确检测学术主张的次级学术领域的标准,因而意识形态的偏好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能施加特别有力的影响。 在缺少用来选择足以证明假设的证据的良好的学术标准的地方,在缺乏对早期研究有所偏爱的价值观念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压倒性的力量可以阻止意识形态对我们——在选择何种学说来作为自己的信仰时——施加自然而然的影响(1991,56)。
这里几乎没有关于范式转变的废话。
把历史主义与范式转变的问题搁置一边不管,对国家(state)的重新重视至少提醒我们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的重要性。我早已指出,许多民族国家是最近的四十年里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在现在也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制度长期软弱无力,尽管边界是人为划定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问题仍很突出,可是这些新的国家已经作为一个地缘实体而存在下去。最近发生在前苏联及其卫星国的事情 代表了一种向前些时代即已明确界定的民族政治单位的回归。
在当今的国际秩序中国家明显是基本的分析单位(e.g.,Nettl,1968)。很明显,当今的国际秩序是一个保守的秩序,在这一秩序内,各国都在维持现状,维持民族国家作为司法主体的制度,并且都认为这与自己利害攸关(Young,1976,81-83;Jackson,Rosberg,1982a;Jackson,1990)。这一秩序被各民族拥有民族自决权和不干涉它国的内部事物的原则所合法化。民族国家因而一直根据国际法来界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们成了本书关注的一个焦点。但这种定义的连续性掩盖了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能力(capacity)的惊人的变化,而我正是要对这种变化加以辨析。
第一部分 政治能力研究的背景第5节 本书的目标
这本书的目标是要澄清一些关系到民族国家政治能力到底由什么构成的问题。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有许多国家脆弱、无效,另有一些看似并非如此脆弱的国家崩溃了——比如伊朗革命,放弃对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统治,黎巴嫩,当然还有前苏联及其东欧保护国。尽管对什么是政治能力还有混淆,但从这些——缺乏政治能力,也就是说,存有政治真空的——例子中,我们就会对它产生一种直觉。我们必须从这种直觉中超越出来,并对政治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有积极的理解。
我的基本观点是制度是政治能力的关键。能力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但为了它的有效性,制度必须是建构在合法性的基础上。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早期的发展研究中了解到很多东西。这些早期的发展研究提出的问题至少和它们已经解决的问题一样多。我们兜圈子兜得不能太多,这一点非常重要。
政治能力不只是包括简单的变化,这一点将会得到明确。我交替使用capacity, capability, development来指代能力,这些词或多或少可以互换。既然我关注的是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我自然要对最近的一些关于国家力量(strength)的著作中提出的问题予以正面回答。本书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political infrastructure)何时才为恰当、相称(in place )”?我们就从“政治活动的特殊性在哪?”这一问题开始讨论吧。
第二部分 何谓政治能力第6节 政治权力的相关特性(1)
所有国家最重要的基础是好的法律和好的军队。没有好的军队,就没有好的法治,这对新国家、老国家或新老混合的国家都一样。
——尼古拉·马基雅弗利,《君主论》
允许我这样说,仅凭武力是不够的。人们可以征服一时,但无法消除再度征服的渴望。不断被征服的民族,也是是无法统治的民族。
我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不确定性。恐惧并不总是武力在起作用,军队也并不总是胜利者。如果你失败了,你就失去了力量源泉,因为,和解失败,武力却可能继续存在,但是如果武力失败了,就没有再度和解的希望。力量和权威有时可以通过仁慈来买到,但它们却不能象一贫如洗的人或战败者乞讨施舍那样乞求得到。
——爱德蒙· 伯克,《论与殖民地的和解》
使用暴力时,权力并不是最有力——反之,却是最弱——的武器。当使用的武器是拉拢、参与而非排外,是教化而非消灭时它的力量最为强大。掠夺、强迫并非政治生活或两性生活中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显示和证明。
——查尔斯·梅里安,《政治权力》
从政治的角度上看,说权力和暴力非同一事物显得分量不足。而应该说它们是互相对立的事物;在其中之一能加以绝对统治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没有生存的余地。
——汉·阿伦特,《论暴力》
在我们对能力(capacity)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对它的政治内涵予以澄清。这看起来有点象入门知识,但怎样对它进行政治学的理解确实存在着很多混乱。在我们对它界定之前,我们先看看政治能力到底与什么东西有关。
我们最好的分析起点是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著作《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怎么得到?》(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拉斯韦尔的标题提醒我们政治与资源的配置和分配有关。我们还进一步记得大卫·伊斯顿(David Easton,1957)认为政治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定义。这些观点告诉我们,政治总离不开因价值性资源分配引发的冲突。
为何冲突如此重要?因为我们关注的价值性资源——收入,权力,声望,荣誉等等——的分配,这些东西正是个人和团体争相获得的东西。如果一个行动者对它们实行排他性控制的话,这些东西本身并无内在价值。在这一意义上,它并不是可去占有的东西(possessive)。可是,这些东西又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relational),也就是说,它们的意义源自于体现它们的环境和至少有其中二者是相互连带的(当然这是最为简单、基本的情况)特定的背景中。此外,这些资源并非均衡地向外扩散并保住自己的社会价值。比如说,如果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声望和地位,那这概念本身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没有其它声望较低的团体的存在,一个团体或组织也就不能享有较高的声望。同样,收入也是这样。收入只能从产生它的地方——其它的团体或个人能用它从别的团体或个人换来产品或劳动——获得它存在的意义。如果每人都有同样的收入甚至是高收入,那么收入的社会意义也就不再存在了。换言之,一个人陷在孤岛中,收入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收入的观念是建构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上:只有在一个足够宽大的、能换取他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经济环境中,收入才有意义。
我们不应简单地把价值性资源视为具有“可资占有特性的东西”(possessive)——它指的是独立于任何外在环境,具有内在的、天生的价值的东西。 团体或个人对这一类东西的占有与他人没有任何关系和牵连。与此相反,被赋予外在价值的东西与它们所处的并给它们带来社会和政治意义的环境密切相关。这些东西的价值源于在个人或团体之间分配的不均衡这一事实。
社会和政治不平等是相互关联的。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大马车的寓言证明了这一点。寓言说,人们正在艰难地拖着一辆马车,沿着一条崎岖不平的沙路前进。位子在马车上部的幸运的乘客不时地——尤其是路变得更加陡峭的时候——对下来拉车的兄弟姐妹们表示同情和怜悯。
必需承认拉车人的惨状促使乘客认识到了在马车上部的位子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并使他们比以前更加绝望地抓住拉车者不放。如果乘客确信没有谁会从车上下来拉车,可能的情况就会是:排除捐赠用于购买药水和绷带的资金不管,他们就会自己动手而不是只让下来拉车的人去干(Bellamy,1887,12)。
换句话说,马车上部的位子的价值不是内在的、与生俱来的,它们的价值只是有人肯下来拉车才体现出来。
一旦我们承认居于政治中心地位的价值性资源具有内在相关性,那么——借用施茨克内德(Schattschneider,1960)的话来说——带有偏向性的流动(mobilization of bias)的政治现象总是会出现。人们没必要采纳认为政治斗争是一些人的收益以另一些人的损失为代价的零和结局的极端性立场。如果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指零和结局),那我们就不能说政治的中心是价值性资源的分配,因为这时这些资源没有任何价值。
政府的主要活动是对居民的收入进行控制。政府有很多机构对税收、公共开支及其规则的制定等进行管理。如果这些机构安于现状,那很明显,政治冲突将使某些人以他人的损失为代价并从现状中受益。另一方面,如果政府通过投资于A部门而不是B部门来改变现状,那么这种选择将使A受益,而B却付出同等的代价。例如,大多数非洲国家实行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这一政策损害了农业部门的利益,那么即使农业部门的收入得以按计划(当然这是难以置信的最佳情况,Bates, 1981)绝对的、长期的保留,它们还是会遭到损失,因为它的购买力相对于其他部门来讲已经下降了。
另外,我们把政治当成是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另有一些人主张政治是冲突的解决。我并不想考察冲突如何用最好的方式加以解决,我只是说冲突是可以控制或处理的。 问题是由谁来实行控制和管理?
很明显,断言冲突是可以管理和控制的人是要借此来突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区别,即管理者扮演权威的角色。换句话说,政治包含着权力差异。象其他的价值性资源一样,权力也是具有相关性和依存性的,并且存在分配不均的现象。但权力包含哪些内容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巴拉奇(Bachrach)和巴拉茨(Baratz)的分析会大有用处。 他们在权力(power)、权威(authority)、影响(influence)和暴力(force)这四个基本概念之间作出了区分。
在他们看来,权力有三个基本特征:它关注的是两个(A和B)或更多的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利益或价值冲突;A对B施加权力,同等程度,B需按照A的意思去做;B按照A的要求从事是因为B害怕来自A施加的有效制裁的威胁(或直接或含蓄)。尽管每个组成部分都是权力实施的必要条件时,但只有当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我们才能说存在权力关系。
与权力不同,权威关系不必包含价值冲突的内容,在这样一个关系中,B按照A的意思去做,是因为B认为A的要求是合理的(reasonable)。这种服从并不源于公开的价值冲突,反之,B和A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他们举了一个关于士兵的例子,士兵服从长官的命令是因为士兵视这些特殊的命令和由总路线决定的命令为合理的。这种关系要有条件,对这一点,我将要在下面的分析中谈到。
影响位于权力和权威之间。与权威不同,在B服从A的要求的同时,包含着冲突。然而影响力的根源并不在于对制裁的恐惧。相反,B按A的要求从事是出于对A的尊重和敬意,或者是B有求于A。
巴拉奇和巴拉茨的区分非常有用,因为它说明了为什么权力必定是取决于其他依存条件的。被监禁的囚犯不可能在午夜对他人施加权力。与此同时,权威和影响也只不过是权力的特殊情况。
权威与冲突无关的思想和政治主要关注冲突的控制和处理的思想完全不一致。我认为这里的关键是利益和价值之间的区分。无公开的价值冲突并不等于就不存在利益冲突。相反,它表明B因为教化或社会化的作用而认为他们一起享有相同的价值并因而享有相同的利益。正如鲁克(Luke,1974, 24)指出的,
难道不是通过权力的作用以改变人民的观念、认识和偏好,通过使人民接受权力拥有者在既存秩序的地位这些最为高明的方式——或者说是因为人民看到或认为已别无选择,或者因为这看来很自然以及这一切的无法改变,或是因为人民把这一切当成上天注定的和有利的——来阻止人民的抱怨和不满吗?我们假定,没有不满和抱怨能等同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真正的一致和共识,但这就过于简单地排除了存在虚假的(或为法令操纵和摆布的)一致的可能性。······
不管这是否高明,鲁克所指的现象中包含有履行权力的成分。总的一点就是,权力的实施决不允许冲突的公开存在。
我们再次分析一下巴拉奇和巴拉茨的例子,就会发现他的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的假定等于是无限延长了人的生命。即使军官能够通过求助于已成共识的、已经内化的评判是否光荣和勇敢的标准的价值观的帮助,以引导士兵的服从,在这种情况下,军官下达的与敌人战斗的命令仍可能与士兵的最佳利益不相符合。并且对于多多少少没能对恰当的行为规范加以内化的少部分士兵来说,提醒士兵说,没有任何一支军队会缺少严明的纪律和程序,甚至包括军事审判都是这样,这非常有用。
第二部分 何谓政治能力第7节 政治权力的相关特性(2)
与此相似,在一个属于影响(influence)范畴的关系状态中,服从之不来自对制裁的恐惧这一点也已含蓄地承认教化和社会化所起的作用。教化包含着道德奖赏和物质鼓励,宁愿选择“胡萝卜”,也不选择“大棒”。但是缺乏明显的对消极惩罚的畏惧,这并不排除B会心照不宣地认为A有能力对自己实行攻击。很明显,当A不明显求助于惩罚时,A并不那么令人恐惧。但在现实的应用中,就很难对影响和权力加以区别。我认为这里最为重要的是权力。
这一结论与最近的一些研究观点一致。克罗奇(Crozier)和弗里伯格(Friedberg)指出:
权力只能通过特定关系中的行动者的交易来求得增长。在这一意义上,两个党派间的每种关系都预先假定二者之间存在着交易和相互适应。权力永远与谈判联系在一起:它是一种交易的结果,因而也是谈判的结果,并且至少有两方卷入其中(1980, 30-31)。
他们接着指出,当权力含有相互关系的意思时,相互性本身并不均衡。换言之,权力需要一种单方依存关系而非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
巴拉奇和巴拉茨对权力和力量作出的区分最为有用。象权力一样,力量也包含价值和利益的冲突。与权力不同,暴力不导致服从,相反,暴力的使用等于是对没有强制就没有服从的一种承认。正如伯克(Burke)在他对美国殖民地进行研究时指出的一样,使用暴力的人事实上在面对不服的情况下仍试图达到目标。此外,因为预计中的牺牲者B可能不担心来自A的制裁,因而暴力并不总是产生顺从。为何会是这种情况呢?因为暴力不必依赖特定的环境而存在,它是独立的、内在的。A有攻击B的财力、物力并不意味着 在A和B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关系。因此梅里安(Merriam)得出结论说,强取豪夺并不是权力的体现。
巴拉奇和巴拉茨得出结论说,制裁的恐吓是权力关系的关键所在:“制裁手段的实际运用等于是承认他们已被想要成为未来的权力拥有者击败”(1970,28)。确实,寻求暴力解决可能导致A的权力的丧失。比如说,B可能会认为制裁也不过如此——他们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巴拉奇他们接下来说,作为一心想要成为未来的权力拥有者的A来说,他们宁愿不选择恐吓这一手段。 这时,恐吓的有效性是关键所在;诉诸于恐吓这一手段也是很不可取的。
尽管这些考虑是最为基本的考虑,可还有几个关系到民族国家政治能力的问题。首先,权力和暴力的区别太容易被模糊。比如古丁(Goodin,1980,3)就声称,可以假定权力的实施有几种方式:“你可以通过强行手段,也可以通过说服他,让他给你钱;你要改变法律结果,既可以通过买通法官、可以通过暗杀他,还可以通过选举把他赶出公职来达到目的。”既然古丁列举的情况并不都与权力的实施有关,那么他把权力和暴力等量齐观就缺乏根基,更何况古丁对合法权力与非法权力的区分(同时可参Beetham,1991)并没有能解答这一问题。
与此相似,格尔(Gurr,1986a,46)认为统治者要提高他们的权威,有很多种可行的选择,从诉求合法性的感情到暴力的使用,无一不可。“在这一观念当中,包括恐怖主义的暴力的使用都是能够借来建构和维护国家权威的多种策略之一。”既然格尔把使用暴力等同于权力的实施,那么问题还是和古丁的问题一样。
最后,杰克逊(Jackson)和罗斯伯格(Rosberg)指出,权力和合法性可以分离开来:“一个政府可以享有合法性,但它的权力机器发挥的作用却可能有限;或者它可能有着强有力的权力机器,但政府在老百姓眼中,却很少有合法性。(1982a,7)。”事实上,这两种区分都无意义,因为——正如我下面将要论述的——权力是具有相关性的,权力的行使要求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这就是那些权力拥有者花费很大力气去使自己的行动和要求合法化的原因。
我的观点与认为权力的研究方法(如上所述)只是一个很少或根本不能适用于其它文化的西方研究方法的观点有着很大的分歧。这一结论是安德森(Anderson,1972)在对爪哇文化中的权力概念进行研究时所得的结论。他认为,在爪哇的文化传统中,权力是具体的、是实在的(concrete),而不是相关性的、依存性的(relational),因而,使用权力的概念没有必要提出合法性的问题。最近派伊(Pye,1985,320-21)指出,权力的概念在不同的文化里,有着不同的内涵:
把“权力”当作是精英的基本特征,把权杖当作是大人物高举在公众头上的东西,把合法性则当作是属于公众、源于公众、公众并借此对他们的统治者进行监视、评判、自下而上的东西,这一切在西方都是很正常的。在亚洲,权力与合法性正好是以相反的方式运作。权力根本取决于下级的支持,而不是凭借上级的意志和姿态凭空产生。而合法性则由那些有着最高权力的人来加以界定。
两派学者都认为权力的内涵由各自的文化来决定,他们关于权力规范的结论都是建构在基本冲突之基础上,这些看起来很有意思。安德森认为权力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具有相关性、依附性的,而在爪哇的文化背景中权力则是独立的、内在的,不依赖于别的东西而存在。另一方面,派伊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在亚洲人的思想里比在欧洲人的观念中权力更具有相关性和依存性。
这是一个把秩序的本质和对政治秩序进行意识形态的辩解混淆在一起的阐述性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例子。用神学标准来解释教皇权威这一事实,并没有模糊罗马教廷作为世俗机构的政治实质。确实,派伊自己也接着承认,“在权力与合法性的创立过程中必定存在着相互的回应,因为二者都是双向街道”(1985,321)。这点已被接受,但另一方面它又削弱了他的关于不同的政治文化在解释政治权力时有很大的意义这一观点。
政治包含权力及权威的实施以及这二者被视为是相互关联的,这有着第二种含义。政治发展的论争(比如亨廷顿,1968)和对国家的论争(e.g., Nordlinger, 1981,1987)都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关注政治自主性(autonomy)这一问题。在此,我们对这一问题要小心对待。政治自主性这一术语使用起来好象它是一个要么包罗万象、要么一无所有极端性的数量问题,其实,政治机构要么是自主的,要么不是:
国家自主性的增长对社会而言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在社会里很少有能阻止政治屠杀的压倒性的权力,因而具有自主性的国家精英也可犯下致命的错误。国家自主性的急剧增长可能导致国家和社会基础之间接触的丧失(Dominguez,1987,69)。
因为承负着认为权力是内在的、独立的太多的错误的理解,这一术语因而显得很让学者们心烦。多明格茨(Dominguez)认为国家已经有效地脱离了它的社会基础。然而要弄明白政治结构如何摆脱更为宽泛的社会力量的控制而获得完全的自主性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当然,如果政治几乎与暴力的使用无关,这一问题也就不再存在。但是,如果我们关注政治权威(如果加以具体化,指的就是国家)如何对它的下级施加权力,绝对自主的问题就无实际意义。确实,权威可以造就出别人服从并与它的偏好广泛一致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从完全的意义上讲——权威真正享有自主性。不错,政治架构相对而言可能是特殊的、可区别的。权威甚至也可能造就出相当程度的一致和秩序。但是,正是权力的相关性、依存性这一特点使得政治权威与广泛的社会力量难以分开地缠结在一起,而且在这一意义上,国家总是“社会的一部分”(Migdal,1987,396)。就这一点而言,在恰当的环境中,政府享有相当大的操纵空间,这正意味着它们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然而,自主性的下限就是它总是受制于权力与权威相互关联这一特点。
第三,有学者把政治的“我们反对其他的人”的定义(politics as us against the other)(Poggi,1978)与政治的“政治是分配”的定义(politics as allocation )区别开来。他们继续认为采纳后一定义就是赞成把政治世界个体化、原子化并且对政治制度的地位视而不见的多元主义的观点。相反,政治的“我们反对其他的人”的界定却把我们的注意引入了更大的结构性的行动者。比如,克拉斯勒(Krasner,1984,224)就认为“国家主义的理论路径更倾向于把政治看作是统治和控制的问题,而不是把它视作一个分配的问题。”
结合我已采纳的政治活动的理念,我们就会发现要理解鲍奇(Poggi)所作的区分实为困难。如果说,政治是要对因价值性资源分配引起的冲突进行管理的话,那么根据这一事实,政治不但包含统治和控制,还包括对资源进行分配。基(V. O. Key)对这一观点有着非常明确的表述:“从长远的角度来讲,政治可以被归结为有产阶级和贫困阶级的冲突”(1949,307)。有产阶级——拥有权力、地位、声望、高收入等——寻求对付包括妨碍和搅乱秩序在内的各种挑战,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控制和分配就必然缠结在一起。
这样结果就是,“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有害概念”(Krasner,1984,232)的弊端也就昭然若揭。“对凌驾于个人和阶级利益上的公共利益的强调”和“对国家作为保护整合与贯彻公共目的之工具的重要性的强调”(Lentner,1984,370)的黑格尔国家学说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用亨廷顿“公共利益无论如何也强化了政府机构,公共利益是公共机构的利益”(1968,25)的话来说,这一观点也就不言而喻的体现了出来。当我们考虑的是“国内”(demostic)政治的时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民族共同体等等的概念上的问题也就变得很明确了。既然政治是指因诸如收入、声望、权力等价值资源分配引起的冲突,既然这些好处相互关联,那么,当一个团体赢得了这些东西,其它的团体必然失去这些东西,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此,根本不存在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
最后,权力(相关性、依存性的)和暴力(内在的、独立的、天生的)的区别非常重要,因为这一区别表明在其它的事物之间,持续的肉体惩罚和物质强制根本就是非政治的。就这一点而言,我并不是说暴力在政治中无足轻重。使用暴力威胁是基本的手段,这一点我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没有暴力,要理解权力如何得以实施就会变得异常艰难。此外,如果威胁确实有效,那么暴力就可以在需要它的时候随时使用。比如,如果一小群逃税者都确实得到了惩罚并且予以公布,那么遭到监禁的危险就可能遏止住大规模的逃税。
除此以外,暴力尤其是在局势危急的时期能发挥明显的作用。最为显著的是在革命结束不久的时期里,革命的成功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惜使用暴力来消灭他们的敌人。在因革命引起的内战时期和军人政治时期暴力的使用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在紧随非殖民化运动其后的时期,也会出现暴力不时使用的类似现象。这些时期使用暴力有着显著的不同,也就是说,它们是在出现政治权威模糊不清或没有得到明确的情况下才使用的。在类似的情境中,使用暴力可能有助于促成问题的政治解决。但是,借助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并不自发形成问题的长期政治解决。因此,正如马基雅维利、伯克(Burke)等人理解的那样,动不动就依赖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并非明智之举。
第二部分 何谓政治能力第8节 政治能力研究的意义
尽管权力和暴力之间的基本区别相对简单,但这一区分并没有使人们对政治能力有多深的了解。许多学者置代议制、民族自决权已成为证明现代民族国家合法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这一事实不顾,仍过于强调暴力在当今政治中的作用。我们还记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国家是唯一合法使用暴力的政治实体”这一经典论断,但还有人回避他“使用暴力并不正常,它也不是国家实行统治的唯一手段”(Weber,1946,78)的话,夸大暴力的作用,却忽略合法性的作用。 这一问题至少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异常明显。
非殖民化运动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在世界范围内输出民主的巨大希望。当然,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最为明显的是军人政治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常态。从1945年起,更多的第三世界的政府首脑是通过军事政变而不是通过选举的方式来实行更替。最初,一些学者非常乐意对军人干政进行研究,是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即非军事组织较为软弱或无法存在,军队最有可能吸引住新兴国家的人才,军事组织采用了一种有助于发展的外在形式,并因而可能提供一种相对的“稳定和控制”(Levy,1966;Pye,1962)。后来的学者对军人政权总是乐于进取、乐于改革这一点更不乐观(e.g.,Huntington,1968; Nordlinger,1970),但却继续认为军人政治可能对后来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当我们回忆起军事政变充满暴力并对国家予以非法打击时,很明显,对军人政权作出这种断言是建构在这一政体能够提供解决政治问题的技术手段这一假定的基础上。 然而,经验事实表明,在解决政治问题上,军人政权和非军人政权的行为是没有显著区别的(e.g., Jackman, 1976; Zuk and Thompson, 1982)。那么这究竟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相信它强化了对暴力和权力作出区分的意义。成功、有效的政体——不管它是军人政体或是别的政体——是指那些能够使权力得以实施的政体,而一开始就依靠暴力的政体却不能说是成功的政体。在许多国家出现的军人政权的意义在于它为那些具有政治抱负的人提供了机会(当然,不仅仅是机会)。但在政客和军人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能有效地使用权力的政客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将会取得成功。与此相反,那些一开始就依靠暴力的军人不管他们是不是通过军事政变来获取职位,在政治的意义上,往往都是失败者。
在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中这种区分更加适用、有效。史蒂潘(Stepan,1985,320)在对拉丁美洲的官僚(bureaucratic)威权政体进行研究时写道:
既然强制是权力的一个格外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国内强制机关的制度凝聚力的程度也就成了一个关键的变量。智利政权在1973年到1981年的近十年间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是强有力的。
但是,如果说暴力的频繁使用是权力丧失的表现的话,那么史蒂潘的第一句话就不能算是一个推断性的结论。与此相似,多明格茨(Dominguez,1987)声称拉丁美洲的强国家(或是具有自主性的国家)与软弱的政体和执政者共存,就显得有点自相矛盾。此外,这一悖论完全依国家力量(state strength)的定义而定。这一定义关注的是国家早已完备的强制能力和日渐增长的军费开支与州际冲突。 如果多明格茨承认暴力象韦伯国家思想中的合法性一样占有中心地位,那么,这里也就不再存在任何理论上的悖论了。
我并不是要否认暴力威胁是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也不想去否认借助暴力的广泛使用可以使任何政权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统治。我只是说,不能无限期的使用暴力,强大的暴力机器也不足以证明政治权力或政治力量的同等强大。
最后,有很多学者对在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暴力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e.g.,Tilly,1975,1985,1990;Cohen,Brown,Organski,1981;McNeill,1982)。有很多证据表明,欧洲国家通过暴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军事征服在北美、澳大利亚和其它移民国家的创立过程中也发挥了明显的作用。此外,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边界也常常说明了这些地缘边界是在殖民统治时期通过各殖民国家的军事竞争来加以确定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仅仅因为暴力在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在现代国家的统治和发展时期暴力依然会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面对着那些能成功的实施权力或权威的政体,当今的民族国家到处面临着扩大政治参与的挑战。权力和暴力的区分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区分,但它对政治生活的意义和影响却是广泛的而又深远的。
第二部分 何谓政治能力第9节 作为合法性制度建立的政治能力
作为一个整体,前面的分析表明政治能力与充满着合法性色彩的政治制度的创建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将在此对它进行讨论。
我早已指出,政治发展和政治能力的概念因为它的目的论色彩和价值负载的原因有时受到攻击。如果我们把政治能力当成是有形或无形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建设,那么这一反对就没有多大的力量。我们再来看看经济发展这一概念。虽然经济发展确实包含着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剩余这两层意思,但许多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的内涵远不止于此。
比如说,一个小国可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并计划开采。这个最初贫困的国家最终能享有最富裕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尽管当地资源已被精密的资本流程开采得一干二净,但提供给当地人的就业机会却微乎其微。我们能说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经济的发展吗?事实是未必如此。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看他们建构的经济基础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如果新创造的财富被投入到象教育、交通或其它与工业化紧密相连的领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某种形式的经济发展正在发生。相反,如果这笔财富被转移到国外的银行帐户上,我们就只能得出不同的结论。经济发展远不止于财富的增长,它还必须包括——在当代而言——与工业化紧密相关的经济基础的建构。
上述评论完全适用于政治能力这一问题。既然政治集中关注政治关系的状况,那么必须有一套能够为容纳这些关系作出结构安排的政治制度。权力的实施要求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换言之,这种关系状况必须能够持续一段时间。权力的实施同时要求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必须规范化。连续性和规范化的要求只有在制度基础的环境中才能实现。克罗齐(Crozier)和弗雷伯格(Friedberg)在作出“制度为组织成员间的权力关系营建了范围并作出了限制,并因而划定了谈判的条件。制度是强加在参与者身上的笼子”(1980,37)这样的论述时,对这种情况有了很好的论证。诺思(North)也作出了相近的论述,他说,“在社会中制度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构一个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uncertainty)”(1990,6)。
因为权力的实施离不开组织,这一思想——如果我们代之以对政治变迁(Huntington,1971)进行关注(请参Ruttan,1991),我们就可以避免被指责为动不动就贴上“发展”标签的尴尬——也就没有多少意义。政治变迁可以包容任何事情。亨廷顿对普利夺政体(praetorian)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政体变迁的描述成了一部描述政体变迁的专著。但这种变迁自身并没有产生出任何政治组织,甚至于对政治组织的产生不无害处。就象经济发展不单指增长,政治能力也不单由变迁构成。经济发展和政治能力都需要制度基础(infrastructure)的不断创建。亨廷顿的“制度是政治发展的中心”这一论点比他后来关于变迁的论点前途更为光明。
但政治能力并不仅局限于此。特别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制度要为权力关系提供一个运作结构,它首先必须具有合法性。可能有人会认为引入合法性的概念只不过是打开了一个伦理道德的潘多拉盒子。但这并非我的原意,我只是在下列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只有当大多数公民倾向于认为对这一制度体系下的政府官员的服从(compliance)是合适的和合理的的时候,这套制度才能说是具有合法性。这样,服从就成了一种习惯。 换句话说,合法性论题关注的是“怎么有些人就被认为是有权统治别人”的问题(Geertz,1972,325)。合法性这一术语在伦理上是中立的。权威可以借助公正的或无耻的方式来获取合法性,而且劝服和操控之间的界线本来就是模糊不清的。 无论通过什么途径来产生合法性,它总是政治能力的核心。
当然,如果政治只是指物质暴力的使用,那么合法性的论题也就毫无意义。但是一旦我们承认权力是政治的中心,承认权力必定是相关性的(relational),那么很明显,制度只有在它们被普遍认为是合法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换言之,在权威实施者和权威服从者之间必须存在一种关系,凭借这种关系,权威的服从者才会承认前者是实际上的权威。对合法性的分析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种关系的实质(请参Lane,1984,209-10)。此外,如果我们认为成功制度的要素之一是这一制度的长期稳定,那么合法性也必须具备稳定性。
对这一问题清醒认识非常重要。亨廷顿把稳定和秩序视为政治发展的首要目标,而我在第一章中早已指出,对稳定和秩序的过分强调引起了广泛的批评(e.g.,Hopkins,1972;O’Brien,1972;Kesselman,1973)。最近,亨廷顿的分析已经被视为发展研究中相对具有权威主义色彩的强国家学派的代表(Randall and Theobold,1985)。从视稳定和秩序的出现为合法性的体现这一意义上讲,这些批评具有充分的理由。 在对政治基础基于发展的中心地位的强调之时,我同样重视稳定和秩序的重要性。连续性是政治活动的关键,这也就意味着稳定问题必须在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开始得到政治解决之前就加以解决(Roth,1968)。但是,我要加上一个附带条件,即制度在被视为稳定之前必须是合法的。
另一方面,对亨廷顿的批评有着纯粹主义的根源。这指的是他的方法(approach)因为把从低层进行观察排除在外而应受到指责。也就是说,低层平民的利益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对亨廷顿的另一个相关的批评是它回避了任何形式的阶级分析(请参Smith,1985)。在这,人们必须非常谨慎以避开把政治能力等同于民主发展的理论陷阱。我曾强调指出,合法性是政治活动的中心,但合法性并不能等同于民主。合法性依赖于无处不在的、使得统治者易于进行劝服和操纵的公民的看法和观念。公民可以通过社会化和思想灌输来接受政治制度。即便我们能够在劝服和操纵之间、或是在灌输和社会化之间作出区分(我和林德布洛姆〈Lindblom,1982〉一样对此深表怀疑),合法性不是依赖于认可和接受如何产生而是更依赖于认可和接受是否根本产生。
我对制度基础(infrastructure)和合法性的见解与史蒂潘(Stepan)的观点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一点将在整本书中明显地体现出来:
制度化指的是:一个政体把新的继承、控制和参与的政治模式固定下来;这一政体试图建构起一个经济积累的切实可行的模式;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全面的统治支持群体;在市民社会中创建了一个具有很高水准的葛兰西主义(Gramscian)的“支配性的、最高的认可(hegemonic acceptance)”。制度化还意味着这一政治体系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多数政治行动者在新的制度框架内通过各种手段去谋求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地位,而不是去对这一框架加以抵制、削弱甚至终结(Stepan,1978,292)。
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
最后,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政治能力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要不是比较政治学的学者倾向于分类学而且分类技术并不十分高明这一事实的话,承认这一点并无害处。比如说,在不久的以前,我们在对现代化理论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区分上浪费了太多的精力和笔墨(Gusfield,1967)。传统与现代的争论引发了许多问题,其中核心问题是:用什么东西来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作出区分?尤其是我们应该在哪给这二者划出一条界线?但值得明确的一点是,即使没有对这两个相互排斥的类型加以描述,现代化理论仍然行之有效。例如,列维(Levy,1966,35)就把现代化界定为“非生命力量资源对生命力量资源的比率”。这一界定通过连续谱(continuum)的方式避开了分类的问题。现代化成了一个度的问题,而且指的是一个结构性的现象。在这种定义下,现代化的政治结果既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积极的。
如果比较政治学家们并不赞成概念的定义必须包括定性分类,那么这一主张——政治能力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就会变得十分重要(Kalleberg,1966;Sartori,1970)。概念分类必须包括定性分类的观点有较长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不同城邦的分类。在这一观点的最近的形态中,它已经成了批评的基础。比如,杰诺斯(Janos,1986,66)就发现发展研究在部分意义上来说是有缺陷的,因为“无论是对于共产主义国家是否属于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社会阶层是否应该根据它们自己的标准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两点都没有达成共识”。正如我在其他的地方多次提到(Jackman,1985),对定性分类的强调却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它将削弱比较政治学的研究。
当政治发展被视为是一个表现民族国家政治能力程度的连续性的表象的时候,这时,这一术语并没有事先假定存在一些终极目标或值得追求的政府形式。相反,这一术语指的是,是这些国家性的制度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必备结构。在这一意义上,能力并非一个要么包罗万象要么一无所有极端性的东西。确实,把能力视为“度”的问题有助于强调政治制度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变得脆弱起来——这点已在政治权力的相关性(relational)这一本质中加以体现。
第二部分 何谓政治能力第10节 早期方法的简单比较
视政治能力为合法性制度的建立只不过是一个开端。即便这样,把我的方法和早期的研究方法作个比较也是很有意义的。我将限定在派伊(Pye,1966)与亨廷顿(1968)这两个著名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之间进行比较。
派伊在六十年代中期就列出了政治发展的十个方面的含义: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代表工业社会的政治;政治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运转方式;行政和法律的发展;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和群众参与;民主建设;稳定和有序的变化;动员和权力;社会变化多向度变化的一个方面。尽管这些定义互相重叠交叉,人们还是会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归纳。派伊还从中提炼出了发展综合征候(1966,45—48)的概念,它由三个基本的要素构成(科尔曼也提出过这一概念)。首先,他认为平等(equality)是发展的核心。平等本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但在派伊的用法里,它包括对大众参与、普遍的非个人化的法律和基于成就而不是先天出身的政治录用的强调。第二,指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capacity),能力指政府的范围和规模,政府的效能,以及公共行政中的理性和世俗化倾向。最后,发展征候还包括结构的分化和差异化(specialization)。
尽管后来有人在发展的经验研究中套用了这些标准(比如阿伯内思,Abernethy,1969),但有迹象表明,发展综合征候的这些界定过于混杂。对平等的强调源于现代化的经典文献,但它模糊了政治制度与更为宽泛的所谓的适用于大众人口的社会模式之间的差别。有些人可能会因为结构分化把保守的功能主义的偏好简单的引入具体分析中而反对将它作为发展的一个征候,我却因为结构分化缺乏明确的现实意义并因而不能应用于实际研究中而反对它。
我和派伊理论中的唯一的联系纽带就是对政治能力重要性的强调。然而我是在比派伊狭窄得多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我所指称的政治能力只是指国家制度的政治效能问题。行政的理性化甚至政府规模的问题(象派伊和其他人使用的那样)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与政治能力并无明显的关联。
与派伊的分析相比,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的四个标准直接地强调制度并明确地排除了象派伊的“平等”要素那样所代表的社会的现代化(1968,12—2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亨廷顿主张政治发展要求具有能适应自身环境的制度。这一制度是相对而言更为复杂的、宽泛的制度。第三,从制度有着独立于社会力量的自身生活的意义上说,制度必须是能从更为宽广的社会力量中获得自主性。最后,制度必须具有内聚性。
因为这是一个更为严格的界定,因此这是对派伊学说的一个推进和发展。但是进一步推进受着一个附加条件的限制。正如亨廷顿指出的,适应性体现在它的长期性。如果我们继续追究适应性的含义(我将在第四章中加以分析),那么更具适应性的制度也更加可能是复杂的,享有自主性的,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内聚性的。因此,如果我们严肃的使用制度适应性这一概念,那么亨廷顿的其它三个标准就显得有点多余。
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到制度适应性的思想与派伊的政治能力概念非常接近,因为制度的适应性与制度的效能是并行不悖的。既然我把政治发展看作为包容了效能和能力的具有合法性的国家制度的建构,那很明显,我的方法也是源于早期的研究。只是我非常明确地注重合法性的问题。
既然我的观点还显得非常一般化,那这意味着这是一个化约式(minimalist)的定义的尝试(与以前的研究相比较)。这也表明了我的这一观点:许多早期的研究的主要缺点是发展的定义过于宽泛。从派伊的结论中这一缺点就有所体现,政治发展被看作是一把看似与工业化和非殖民化进程密切相连的政治、社会、经济变迁的包罗万象的巨伞。这种无所不包的观点的危险在于政治发展这一概念成了一个一无是处的钝器。我对政治能力能被简化为一个单向度的概念深表怀疑。如果要使这一问题变得容易些,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化约的、限定更为严格的研究方法。
第三部分 近期关于国家和政治能力的研究第11节 作为政府规模的国家力量
朕即国家
——路易十四
我已经指出国家的政治能力取决于合法性制度的建构。从表面上看来,这一观点好象与近期的民族国家的研究尤其是与那些国家力量(state strength)的研究颇有共同之处。是的,我在第一章中就已表明这些研究已经把我们带回到早期发展研究研究过的许多问题。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能帮助我们理解政治能力的近期的成果。
首先,我已经强调过作为法律实体的民族国家与国家力量之间的区别。国家的法律定义有两条标准:国家有固定的版图,在国家有权与它国发展关系的意义上国家是独立的、拥有主权的(Brownlie,1979,73-76)。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能限定我们所关注的分析单位的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定义。这一法律属性在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中是一致的。
当然,就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定义仍有分歧,因为主权包含有国际社会的承认的意义,并且在现代的国家体系中这种承认并非普遍。比如,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尽管都是联合国的会员签字国,但直到1991年末它们实际上并没有为国际社会视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甚至只是在潜在的意义上也是如此。象六、七十年代的南越或八十年代的阿富汗这样的附属国的主权至少也是问题重重的。另一方面,台湾在1971年丧失联合国会员国的地位进一步增加了台湾作为主权国家法律地位的模糊性,尽管这个国家仍然与其它许多国家保有着外交关系。与此类似,南非共和国在1974年虽然没有获得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资格,但它仍然保留着联合国会员国的法律地位。 这些情况提醒我们法律地位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并非所有国家都拥有这一必不可少的东西。关键在于这些例外构成了总体中的极少数,虽然就它们而言,会员国的地位非常重要。显然,大多数国家符合法律地位标准。
与此相比较,国家力量的问题与政治效能(strength)和政治能力(capacity)密切相关。这一问题(法律地位的问题)的提出直接表明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具效能。因此,在法律地位作为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相对持久的因素(在当今民族国家体系的背景中)的地方,对国家力量的考虑也就把一个或者更多的变量孤立起来了。
在此书中,我将就国家力量问题的两个基本的视角逐次进行研究。第一个基本视角把国家力量等同于规模(size),因此,强国家就是那些控制了更多资源的国家。第二种视角回避规模问题而把国家力量想象为获取独立或自主决策的能力(capability)。
把国家力量与政府规模连接起来的思想在有些时间里非常盛行。卡诺伊(Carnoy)在《国家与政治理论》(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一书中直截了当地论述道:
这是一本政治学专著。是一本关于政治在塑造当今世界社会变迁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学的专著。在经历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之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不再是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要求的资源的充足和有效配置的问题。产出的方式、何谓产出、产出什么以及由谁决定发展政策是今天颇具意义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就象在生产领域里一样在政治领域里得到解决。
政治学颇具重要性的另一原因是:随着经济的世界范围的发展,公共部门——在此指国家——在每一个社会中(无论是发达的工业社会还是第三世界的原料出口国)、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不只是在政治领域,还在经济领域(生产、财政、分配)、意识形态领域(教育、媒体)、法律执行领域(警察、军队)都变得日趋重要起来。国家影响为何增长、如何增长的问题已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的社会科学家的(或许是)关键话题。国家掌管着经济发展、社会安全、个人自由的钥匙,并通过日渐增长的复杂的工具掌管着自身的兴衰成败的命运(Carnoy,1984,3)。
在这段论述中,国家被定义为公共部门,国家力量或国家能力也被直接等同于政府规模。政府对资源实施控制的范围越广,国家也就越强大。此外,既然政府规模是根据公共部门的标准来加以衡量,那资源力量就只是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而言。公共部门越大,国家也就越强大。公共部门的准确所指是什么呢?有时它指的是政府雇员的数量,但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它据预算标准要么指政府财政收入要么指政府财政支出。公共部门还有政府消费与所有消费之间比率的意思。这一比率增加,公共部门的规模也就越大,因而政府的力量也就更为强大。
在这个意义上,这一视角有很多地方值得介绍。我早已指出,政治关注的是那些更多时候指的是经济物资的价值性资源的分配冲突。此外,公共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对公民收入的控制。卡诺伊坚持认为,把能根据经济准则来加以解决的简单的生产问题视作政治的中心问题要更为合适些。在这一情境中,把国家力量视作公共部门的规模有着充分的外在感召力。
与此同时,卡诺伊的观点掩盖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尤其突出的是,他的政治在当今世界日趋重要的观点假定了在不太遥远的过去政治多少显得并不十分重要这一事实的存在。换言之,他的观点告诉我们,在现在把生产和消费问题视作政治问题更为合适,而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指出是哪一段时间)这一问题被合理地理解为经济问题,而且资源配置被理解为根据效率原则由市场决定并加以解决的。因此“政治的地位日趋重要。”
现在民族国家真的成了一个预设为为自身存在而拥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技术水准的实体、甚至是法律实体的东西。确实,人类学家已经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技术非常原始的没有国家的社会(e.g.,Southall,1968; Mair,1977)。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与那些无国家的社会没有任何关联。与此同时,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民族国家的公共部门急剧增长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政治同时就变得更为重要。它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们政府在提取经济资源的时候变得更为有效。尽管制度基础已发生明显改变,但这在路易十四时期和今天的法国政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现代希腊和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差别并不能说明二者之间政治活动水平之间的差别。政治总是发挥着中心作用,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
尽管卡诺伊为国家力量等同于公共部门规模这一观点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公共部门规模这一概念本身并无普遍性。不错,公共部门规模这一概念是先于国家力量受到重视。尽管这一事实未被承认,但公共部门规模在政治发展研究传统里被很多学者例如多伊奇(Deutsch,1961)、阿尔蒙德和鲍威尔(Almond and Powell,1966,p193)、拉斯托(Rustow,1967,p289)和爱克斯坦(Eckstein,1982)视为反映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1970年,施威尼茨(de Schweinitz)提出了政治生产总值(Gross Political Product)这一概念。它即使不能等同也是近似于经济学家的政府物资和公共服务支出的概念(1970,p526)。与此相似,柏伊姆(von Beyme,1985,p12)也根据政府规模的标准来定义国家力量这一概念。在他的思想中,国家被视作政治——行政系统。而哈里斯(Harris,1986,p145-149)则把国家等同于公共部门。
与之类似的是,人们常常认为,因为工业化对提高财政能力有着巨大影响而在现代国家的形成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比如阿丹特(Ardant,1975,p220)就断言“工业力量就通过给国家提供财源,更确切地说是通过提高财政能力的方式来影响国家权力。财政制度是经济基础进入政治结构的引导者。”这一结论提醒我们,象民族国家一样,公共部门也是一种现代形式。
考虑到这些,我们就会明白,在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和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一系列研究中根据公共部门大小的标准来想象国家能力,一点也不觉得奇怪(e.g.,Rubinson,1976,1977;Rubinson and Quinlan,1977;Weede,1980;Weede and Tiefenbach,1981;Moon and Dixon,1985;Rouyer,1987)。这种解释与卡诺伊的解释非常相似。例如,鲁宾逊(Rubinson)就这样论述:
政治控制或者说国家力量指的是国家支配居民行动的程度。既然暴力是一个并不稳定的施加控制的方式,那强国家就是那些把暴力转换成了一套——能赋予制定规则的权力和对本国居民施加控制行动的——稳定的权威关系的国家。这样,强国家的标志就不是军队的规模或者权力集中在寡头手里,而是国家机器把制定规则和对经济行动施加控制权力中最为重要的控制权占为己有(1976,641—42)。
鲁宾逊的暴力不构成国家力量基础的观点与我在第二章中的论述完全一致。更为有趣的是他把政府制定规则和控制经济活动的能力与国家力量等同起来。而且正是这一等同使得他接下来把国家力量的操作性的定义界定为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把前面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的联系结合起来考虑,这意味着国家力量实际上是公共部门规模的增长。
与卡诺伊相比,鲁宾逊的观点并不包含随着公共部门的增长,政治多少变得更为重要一些的意思。相反,它只是表明随着技术的不断变迁,政府能力也在不断增长,现代国家比它的前任更有能力施加政治控制。即便如此,这一概念仍然遗留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如果我们承认公共部门的规模是国家力量的体现,那么在选择可行度量标准之时还有很大的实际困难。其二,更为根本的是,它将导致在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作出区分的更大的困难。现在让我们依次探讨这两个问题。
第三部分 近期关于国家和政治能力的研究第12节 度量公共部门规模不同方法的比较
政府花费很多时间去制定预算,而且在很多国家也实行预算统计制度。最为著名的是联合国统计局和其它组织比如世界银行提供一年一度各国年度预算帐目统计数字(e.g.,World Bank,1983)。这一系列的最后一本书《世界政治和社会指南手册》(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花了一章的篇幅分析“政府规模和资源配置的问题”(Taylor and Jodice,1983,1:chap.1),并报告了各国政府耗费国内生产总值的大概数字(包括政府在一些选定的领域比如教育和军事上的开支的数字)。该手册列出了一些关于公共部门(反映政府规模)的数字,这些数字也常常被当作国家能力或政治能力的一种体现。
预算理所当然地是政治的体现,并且人们经常认为不同的结算体制阻碍了国家间的比较(e.g.,Taylor and Jodice,1983,1:1-4)。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与其他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的比较更为艰难。于是,联合国和其它的国际组织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建构一套共通的清算制度以利于国家间的比较,而且种种事实表明,这种努力已经增加了国家结算的可比较性。显然,这看来足以证明公共部门规模的数字能够度量国家力量,也说明公共部门规模评价标准的可相互转换性。
不幸的是,这些标准之间的相互转换性并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我将对三个众所周知又互不相同的评估体系进行比较。第一套评估体系是世界银行的一般的政府消费(World Bank,1987,table 5);第二套明显不同的评估体系是由萨默斯和赫斯顿提出的(Summers,Heston,1988);而第三套评估体系是由美国军控和裁军委员会(United State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1990)提出的中央政府支出的评估体系。
世界银行是这样定义一般性政府消费的:
一般性政府消费是指政府实体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所有的开支:包括中央政府、地区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开支;独立运作的社会安全基金;在一国版图内国际权威组织摊派的费用或政府性运转费用。它不包括公共非金融性企业的支出和公共财政机构的支出。当前一般性的政府支出包含以下具体内容,即政府雇员的工资,物资(不包括土地和其它可贬值的资产)购买费用和从经济、军事装备部门有偿的服务费用,其它的政府购买海外商品、服务的费用。国家防务财政支出(不含国内防务)被视作政府正当消费,而所有形态的支出(包括国内防务费用)都被视为国内总投资的一部分(World Bank,1983,1:xi)。
萨默斯(1988)和赫斯顿给出相近的定义来支持自己的看法。世界银行和萨默斯观点的主要区别在于萨默斯他们用市场价格而不是国际汇率来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它的各组成部分所占份额。 与此相反,美国军控和裁军委员会提出的政府规模的评估体系指的是中央政府的消费。这三套标准体系中的政府规模指的都是政府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
既然类似这些体系度量政府规模的标准可以互换,那人们就会以为它们彼此密切相关。然而,正如表3.1所揭示的它们的简单的相关性,这些证据使人们对这一看法产生误解,认为甚至在市场经济国家和被排除的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体制的国家的政府规模度量标准之间
表3.1. 度量公共部门规模的三个标准间的简单成对关系,1985
世界银行的政府消费1.0 100 106
萨默斯/赫斯顿的政府消费 0.661.0 103
美国军控和裁军委员会的政府消费0.710.381.0
世界银行 萨默斯/赫斯顿美国军控和裁军委员会
注:矩阵斜线下方的数字是相关系数;矩阵斜线上方的数字反映的是这些系数基础的案例数。
也有这样一种相互关系(世界银行和萨默斯的报告均没有指出后一种情况)。诚然,这三个体系之间密切相关是无可怀疑的,但这三个度量标准之间的互换性假设要求的远远不止这些。考虑到这是针对同一概念的综合指标,这些关联性的最明显的特征也就是这种相关度本身的恰如其分。
表3.1中的数字当然只是解说性的。然而从扩大它的覆盖面——把其它政府消费和其它年份也包括进去——而不至于使我们得出不同结论的意义上来说,这些数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说明这一问题的有代表性的图式。一个关于简单相互关系的矩阵图并不构成一个能说明清楚的度量模式。另一方面,手头的这些数字也不能为我们发展这一模式提供基础。
当我们考虑到经济发展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时,说这些反映政府规模的指数可以互换就变得更难以站住脚。一百多年前,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深刻指出他的著名的“规律”:公共经济的扩张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直接相关。这一主张此后一致直引人注目(e.g.,Pryor,1968;Chenery and Syrquin,1975)。至少,这一观点告示了我们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规模三个指标的任何一个之间的确切的联系。
此外,这些证据也不具有说服力。正如表3.2所显示的,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政府消费的数字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是肯定的但也是微弱的;萨默斯和赫斯顿的观点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是负面的而且也是微弱的;美国军控和裁军委员会的观点才与发展有着不容置疑的关联。甚至这最后一种联系也是分量不足:经济发展只能说明不到18%的中央政府支出的差异和不同。换言之,用这每一个标准来衡量公共部门规模获得的是根本不同的结果,因此不能把它们视为是衡量国家力量和政治发展的等效的度量标准。
表3.2. 度量公共部门规模的三不同个标准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简单相互关系,1985(圆括号里的数字是国家个数)
世界银行的政府消费+0.26 (104)
萨默斯/赫斯顿的政府消费 -0.27 (108)
美国军控和裁军委员会的政府消费+0.42 (115)
人均GDP的对数(log)
这些结局使得那些相信国家力量能通过度量公共部门的规模来轻易测度和相信公共部门规模能以类似的方式轻易测度的人垂头丧气。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表3.1和表3.2中的数字是在把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体制的国家排除在外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这意味着这些微弱的相互关系并没有因为研究这一难题——测度那些很少存在私有经济活动的国家的公共部门规模——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而降低它的价值。
在公共部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奥甘斯基(Organski)和库格勒(Kugler)提出了另一个测度政治能力的方法(1982,chap.2)。他们认为政治能力(capacity)要靠向社会渗透和从社会提取资源才得以存在。他们进而继续指出征税能力是政治能力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他们又认为税收与生产总值的比率这一普遍使用的测度方法不能完全胜任测度这一功能,因为它忽视了那些足以影响征税能力的全国范围的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既然政府税收与政府消耗有着明显的联系,那么奥甘斯基和库格勒的观点就完全能够适用于前两个表格所使用的测度国家力量(strength)的那些指数。
因此他们认为在税率用来测度政治能力之前,税率这一概念需要因征税能力的国家间的差别而加以修正。奥甘斯基和库格勒在三个特定方面进行了修正。第一,既然在出口部门税收更容易收取,那么,源于出口的那部份国民生产总值就应该加以控制。第二,因为税收更难从农业(尤其是自给农业)中收取,那么源于农业的总产值中的那部份,也就必需考虑进去。最后,既然矿产业与其说是体现了生产力,不如说是幸运,并且采矿业更易通过行政手段收税,那么生产总值中的这一部份也就应该得到修正。
为了得到国家税收能力的数字,奥甘斯基和库格勒从这三个方面的税率反过来来预计税率百分比。政治能力就可以通过观察到的税率与预计的税率的比较来加以测度。
政治发展= 观察到的税率/预计的税率
当这一比值接近“一”时,政府的征税能力就达到了自己预期的水平,并且也有能力这么做。然而,偏离“一”的情况被视为是政治因素作用的结果。比值超过一则增加了政治发展的水平。另一方面,
在一个国家征税低于预期水平的情况下,人们把征税水平的下跌归因于政治体系中完成这一任务的结构的能力缺失…社会的需要如此强大以致政府精英必须在政治能力的限度内征税,(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想法非常合理(Organski and Kugler,1980,81)。
奥甘斯基和库格勒的视角是对使用没加修正的政府支出或消费数据方法的明确的提炼。 他们的方法在这一独立存在的背景中——这一背景产生了这一方法,也就是对国家能力的差别对国际战争结局有何影响进行分析——是很有意义的。不管这一方法是否能界定政治能力,然而,更多的情况下,它不具备这种效能。因为我早已详细说明了,民族国家外交政策中的军事能力与对内的政治能力并非能够相提并论的。这里有两个特定的问题。
首先,正如奥甘斯基和库格勒已经承认的,税率作为测度国家能力的标准能适用于工业化国家这并非是不言而喻的。他们解释说,瑞典的税率高于美国的税率并不反映发展水平的差别。它反映的只是一种风格上的差别,更准确地说,是国家政策的差别。既然很难假设政府征税的限度仅仅是因为来自公民的压力,那么作为测度国家政治能力标准的税率,在第三世界国家同样不适用。如果说——我在第二章中已经讨论过——政治是集中关注价值性资源的分配冲突的话,那么很难认为,在国家公民的诸多要素中,“公民压力”的很少存在会是公共政策的总的推动因素。而且,因为价值性资源在国家内总是分配不均,那种给政府带来“压力”的组织 也并不是在穷国中才会存在。 然而,把国家政策的差异与国家力量的不同混为一谈,事实上这在近期的很多著作中非常普遍。回头在本章中的后头我会有所论述。
第二,无论我们是否关注作为国家力量指标的政府税收还是政府支出,也无论这一标准是否得到修正,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划清公共部门边界的问题。这一问题压倒一切。因此,使用我已界定的财政数据来解决这一实际问题的尝试与对国家力量的分析就会显得毫不相干。那就是说,不存在最好的财政数字能反映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不同。那么公共部门和私域部门的界线在哪里呢?
第三部分 近期关于国家和政治能力的研究第13节 寻找公共部门
表面上看来,容易在公共部门和私域部门之间作出区分。例如,我们可以把非市场消费当作公共性的消费,而把市场(或获利指向的)消费视作私域性的消费。这一鲜明对比确实是世界银行和其它机构使用的公共消费概念的基础。此外,尽管要把这一标准运用到所谓的非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形态正在迅速的消失)国家或运用到那些拥有一个庞大的维持生存的部门的国家会显得勉为其难,但最少,这一区分完全能够应用到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去。
当我们去思考如果没有政府的存在经济将会是什么样子时,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政府的作用无处不在,因此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当然,人们可以估算特殊的公共政策对特定的经济结果会有何种影响。但既然不存在能摆脱政府影响的国民经济,那么要评估政府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会有何种总的影响也就缺乏评估的基础。
此外,所有的政府政策都会产生一种连锁反应,这一反应能渗透到私域部门各个角落。把它称作连锁反应是因为它们的意思是指公共政策对市场行为主体的影响。这样它们就使我们对市场行为和非市场行为的准确区分变得模棱两可。而且这些影响的总的规模也无法精确测量,因为我们缺少一个违背事实的基准。请看下面的例子。
由于各种原因,瑞典的政府消费要比日本高得多。当然对它们之间的准确差别的评估会不断发生变化,但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提供的数字表明,在瑞典,政府消费占了GDP 的60%,而日本的政府消费只占GDP的30%,与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最低的西班牙无甚差别(Cameron,1982,p49)。但这并不意味着瑞典的国家力量是日本的两倍。事实是除了能说明国家政策的不同外,我们不能准确弄清它到底还表明了什么。
人们常提到的五十年代初发生在日本的经济奇迹实际是日本政府高度干预经济的结果。这些干预通常来自诸如财政部、国际贸易和产业部以及大和银行(Bank of Japan)这样的机构。政府的干预是广泛的,它集中体现在制定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计划上。这样,控制进口的政策就被预定为严格限制制成品流入日本,在日本,这样的政策的意义要比在其他发达国家深远得多。政府拥有主要产权的大和银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为集中化的,也是独掌金融和信贷资源的日本唯一的一家银行。该银行与财政部关系也异常密切。
此外,通过许可证的签发和其他的方法,政府在决定哪个产业应该、哪个不应该得到鼓励上也发挥着主要的控制作用。确实,这种控制深入到具体鼓励哪个产业和企业的决定中了。比如,建设任何新的码头、新的石油化工企业、甚至建造新轮船的吨位都需要国际贸易和产业部的授权。直到1974年,所有的技术进口协定都需要国际贸易和产业部的审查以确保进口的只是必须进口的技术,确保某项技术一旦进口,能且只能在那些最能从中获利的公司使用。与此类似,日本还对进入本土的所有外国资本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要对日本的经济政策有较深的了解,请参Pempel,1978;Johnson,1982a)。
当然,日本的产业政策是在与主要公司的利益的协调中发展的,这是事实。但日本产业政策的发展历史与日本缺少国家能力这一观点根本不相符合。所有这些事实说明的是相反的情况,那就是公共部门和私域部门是紧密缠结在一起的。因此人们常常听到关于日本的情况是它的集团公司。尽管相比较而言从这些数字看来日本的公共部门规模较小,但日本的国家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因此说日本的国家能力是瑞典的一半并无根据。 反之,我们很难想到有哪个国家的国家能力会比日本更为强大。
试图把公共部门的规模孤立起来将产生的问题并非在日本个案中才会出现。根据卡麦伦(Cameron,1982)的描述,美国的公共部门的大小与日本的很是相似。尽管如此,要对公共消费和私域消费加以区分非常困难。比如,象其他的市场经济一样,美国给农业提供补贴以对种植什么作物和种植多少发挥直接影响。在其他所有的经济体制里,税收政策给某些形态的经济行为提供强大的刺激,同时也对另外一些“市场”行为者进行打击。
上述情况表明,公共消费和私域消费的区分很难继续下去,甚至我们把注意力限定在那些最容易作出这种区分的经济形态中也是如此 ——这里指的是西方的工业经济。当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扩大到包括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所谓的非市场经济时,这一问题将几乎成几何级数的增长。
与工业化国家相比,次撒哈拉地区的非洲国家的国家能力总被视为弱小的。这种观点有很多原因,包括最近的非殖民化和个人统治的延续(e.g., Jackson and Rosberg,1982a, 1982b)。但即便在这一背景中,公共部门的规模也很少能为准确了解政治能力的水平提供什么启示。尽管它们的政治能力明显低弱,但非洲国家的政府已经表明它们具备熟练运用经济政策的高超能力。要把公共消耗从私域消耗中分离开来,这在非洲次大陆象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困难重重。
贝茨(Bates,1981)在他的一项重要的研究中分析了在以农业经济(粮食主要对外出口)为主的许多非洲国家里市场是如何进入政治舞台的。在这一舞台,政府运用管理的和财政政策的手段控制农业生产者的行为,这些手段与生产者(农民和小农场主)的物质利益总的不符。最为明显的是,尽管农业生产对它们而言非常重要,可是一些非洲国家想方设法把资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区域,以便实行工业化,并对城市中心实施控制,建构政治支持。借助垄断粮食对外销售——农民必须出口他们的谷物 ——的销路,即通过垄断买方市场,控制农民的产品销售,农业私人生产者被得到有效管理和控制,资源也就产生了。尽管最初是打算为农民准备抵抗世界粮食市场价格冲击的资金,但对外销售后来日渐被政府用作向农民征税的手段——政府通过以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价格水平来向农民低价收购谷物,即垄断收购价格。这样,在粮食的外销中就能产生出可以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资源。
贝茨的分析值得注意,因为它强调了公域和私域区别的宽松性。在发达经济中,公共部门通过向私有经济提供补贴来影响私域的经济行为,而在穷困的二元经济中,公共部门则通过管制和开支来影响它们。但是贝茨的研究与那些认为所谓的私域部门——也就是市场——借助某些手段使自己既居于政治舞台的中心(在此,冲突经常发生)又成为实施政治控制的机构的人相比,又引领我们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样,公共部门的规模就变成了一个度量政治能力的经不起推敲的指标。即便我们能够准确区分公共消费和私域消费(或者产品),可贝茨已经指出政治不只局限于公共部门。
当我们考察非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时,我们将遇到同样的困难。我早已指出,东—西公共部门规模比较产生的部分问题源于各国不同的结算制度。诚然,因为这些差异,一些原始资料(比如World Bank,1987;Summers and Heston,1988)没有把有关数字计入非市场经济国家中。这样,在市场被官方贬低为一个次要角色的经济里,私域消费(或市场)的内涵当然就天生模糊不清了。
运用这些最为可行的数据进行的细致评估告诉我们,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国家的政府预算与财富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预算规模也大体相当(Pryor,1968;Bahry,1983)。但是,考虑到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私域消费的地位非常模糊,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预算体现公共部门规模的程度因而并不清晰,因此,要进一步推论就变得更为困难。于是,在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的国家中,国家预算或公共部门对国家政治能力的影响就更为模糊不清。
总之,不管在何种经济制度下,国家力量与公共部门的规模完全一致的观点很难说服别人。鲁滨逊(Rubinson,1976,p642)认为强国家的标志是它控制行动的、尤其是“管理和控制经济行动”的能力。卡诺伊(Carnoy,1984)对此有着相近的看法。然而,事实表明这一能力并不是公共部门的一个简单的功能。伴随着公共消费和私域消费区分的模糊不清,这意味着本章开头讨论过的通过提炼作为国家政治能力指标的财政规模这一手段也不能说明国家能力与公共部门规模完全一致。
第三部分 近期关于国家和政治能力的研究第14节 作为国家自主性的国家力量(1)
依赖政府规模评价国家力量的研究的一个可取的特征是,它能使用明确的标准去界定国家力量。但这并不是国家力量研究的唯一方法。现在我要重点探讨的是,并不首先依赖于政府规模的国家政治自主性这一问题。
当今对国家自主性的研究兴趣可以追溯到那些源自卡尔·马克思尤其是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总的看来,马克思和韦伯都把民族国家视为政府和行政的组织体系。尽管如此,他们两人的观点却截然不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角色模糊不清,在国家如何从更宽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中保持自主性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尽管国家被看作一个特殊的组织,但它只是一个附带性、依附性的组织,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为统治力量——这一力量源于建构在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阶级关系——合理化服务的超级组织。因此,国家的自主性必定是有限的。
与马克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韦伯断言政治活动本身具有独立性,因此不能把国家降格为一种超政治的现象。不错,韦伯的大多数学术研究被看作是在他与要重构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学者之间的一场学术争论(Zeitlin,1990)。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一样,韦伯把国家当作是一个有固定版图的、唯一享有合法使用暴力权力的政治和官僚组织。这一政治和官僚组织具有独立于外界社会和经济力量(它居于韦伯分析的中心地位)的自主性,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确认这一点也是他为削弱经济决定论——这在他看来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的通病——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他对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教伦理作用的分析,以及他对文化力量重要性的极度强调是他作出努力的另一部分)。
考虑到韦伯对政治独立性的强调,那么无论在早期发展研究还是近期的国家主义者的研究里,韦伯的总体性的国家概念成为后来这些研究的核心概念一点也不奇怪。我并不是说近期的研究都彻头彻尾地采用了韦伯的研究视角。因为韦伯对待理性这一概念极为宽松,因此当今的学者在研究时尽量避免那种韦伯式的对作为理性秩序和组织的官僚机构的强调,这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他们只是要对“政治是重要的”这一更为根本的理念加以保留。正如布来特和哈定(Bright,Harding,1984,p3-4)论述的,
国家保留着一套独立自主的、不可缺损的制度,但是,国家是一个内部理性化了的免受大众影响的或只接受自定规则管理的官僚机构这一观点已经为另一观点所取代:国家是一个制度化、程序化了的政治竞争的大舞台,在这一舞台上,同时代表精英和大众的地位、身份、政治冲突一一得到表演和体现。
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一观点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问题是,它并没有向前发展多远。反之,国家只是被简单地视为产生政治冲突的舞台。如伊斯顿(Easton,1981,p317)指出的,“把国家一词只当作政府、政治权威或政治精英替代物,并不会带来更大的损害。”他继续指出,同样,这一术语并无多大的特色。
当今国家主义者对国家中心地位的强调只不过是对“政治是重要的”这一观点的一种论证。这样,关于在发展进程中国家有何作用的文章的介绍,只是要对这一观点加以论证:当今国家中心主义研究的特点,“源于他们各自进行发展研究时恢复政治自主性对他们的发展研究的意义的努力尝试。”(Kohli,1986,17)。
把政治是否完全独立于其他的组织这一问题搁置一边(请参我在第二章中的分析),就会发现,政治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观点是一个非常容易为政治学学者接受的观点。确实,许多政治学家对自己的研究会产生一种只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的感觉。从这一意义上说,韦伯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一些国家主义者的研究当然力图做得更具特色一些。然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可怕的国家具体化——据此,国家被看作一个力图把自己意志强加于外界身上、并保护自己利益(这一利益与其他的政治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单一的、完整的、统一的行动者——的问题。然而,当我们研究国内政治时,要把国家政治权力角斗场想象为一个统一的行动者,这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这些努力将遇到直接的困难。
比如,科比(Korpi)就认为国家非常重要。尤其,他认为在工业化社会内,国家在重新分配财富和其他物质资源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只是阐释了有关的问题。请看下面的论述:
国家可以被视为一个在某一社会中,阶级团体和利益集团进行竞争时形成的制度组织体系。这一制度组织体系的关键方面在于,是这一制度体系决定了确定谁来代表整个社会合法地进行决策并加以实施。我们不必把国家看成是一个独立的行动者,或者把它看成是无论哪个集团都想把它置于自己控制之下而加以使用的一个纯粹的工具。既然这一制度体系和国家能用来对诸如社会分配过程等发挥影响,那么这一制度体系也会影响到权力资源的流动方式,并反过来会受到权力资源使用的影响(Korpi,1983,p19)。
这一论述至少提出了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科比坚持认为国家不应具体化——也就是说,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独立的行动者或纯粹的工具”。如果国家不是一个行动者,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简单地忙于‘国家、劳工、资本三方社会妥协’(Korpi,1983,p25)过程的东西,因为任何这种形式的认可都是在对它具体化。第二,尽管科比暗示国家不只是由现任政府和它的行政活动所组成,他还是认为国家能置于一个或多个社会集团的控制之下。但这一主张使得在国家和政府之间作出的任何区分都经不起推敲。确实,一旦科比使用国家一词来完全代替政府一词,那么分析就变得简单易行了。
在其他的研究中这一问题同样明显。伊肯伯利(Ikenberry)通过关注三个不同国家的政府行为(Ikenberry,1986a),来探索民族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国家一词为政府一词所取代,国家也被视为国内或国际的关键的行动者。作者的国家观念仍然是来自韦伯,尽管他附带了这样一个条件——国家是由文职人员治理的组织,是一个所有事情都是平等的并将继续存在的组织。伊肯伯利继续论述道:
使用“国家组织”这个词和使用“国家精英”这个词来界定国家的逻辑属性是完全一致的,国家精英一词只是国家组织一词的转喻。除此以外,当探究国家的经验性问题时,谈到精英也不无裨益。而且,因为这篇文章关注的是国家战略——或国家政策的自觉抉择,研究者最终都必须面临决策由个人作出这一事实。不过,这种抉择出自国家在更大的国际国内结构体系中的组织地位(Ikenberry,1986a,p55)。
这告诉了我们关于国家的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国家不应直接定义。相反,它只能通过转喻的方式加以描述——也就是要借助其他自身的更为宽泛的概念来代替国家的本质属性和附属特性(也就是说,是由哪个集团来统治它),因此,当伊肯伯利使用国家这一概念时,他的真正意思是指国家精英(即政府官员)。而且,他认为在对国家进行经验性的思考时,这一途径特别有用甚至是一个必备的途径,这意味着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国家没有明确的、特殊的经验意义。然而通过认识到是个人在作出决策,这一途径看来可以避免国家是一统一的、一致的行动者的问题,伊肯伯利求助于转喻这一事实对此作出了批判,因为它意味着只根据国家的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标准来定义国家。此外,国家不只是由政府和政府官员构成的。 虽然认为政府由国内和国际因素决定它的行动是完全合理的,但国家主义者的术语学并没有给这一研究增添任何东西。
在对墨西哥政府和跨国公司妥谈(bargaining)的研究中,一个类似的问题产生了,而且非常严重(Bennett和Sharpe,1979)。尽管自称是国家主义的研究,但是国家和政府这两个词的交替使用贯穿全书(哈格的著作也有类似的缺陷,Haggard,1986)。在该书的结尾,制约国家权力实施的因素也得到了考虑:
当权力冲突中的行动者是集体而非个人时,在潜在权力的运用上可能会有组织的制约因素。由于内部的原因,行动者可能无法动用全部的潜在权力,而这一潜在权力在理论上又是可行的。对于类似国家的复杂的实体而言,这种内部的制约因素可能是因为缺少支配权力以发挥全部效能所必须的组织协调所致(Bennett和Sharpe,1979,p83-84)。
组织协调的缺乏又是由于政府各部门的竞争、各部门内部的竞争以及总统不能为国家政策提供明确的引导和支持所致。
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诺德林格(Nordlinger)的观点,他形成了一个“得到修正的韦伯式的国家定义:”
国家是指占据了能赋予他们、也只赋予他们作出决策并实施决策权威的公职人员个体的总和。他们通过作出和实施决策来把领土范围内的任何一部分居民和所有的居民连接在一起。国家由,也只是由那些被授予社会决策权力的个人组成(Nordlinger,1987,p362,斜体为原文所加)。
第三部分 近期关于国家和政治能力的研究第15节 作为国家自主性的国家力量(2)
诺德林格非常强调国家作为个体总和这一点,这是为了避免把国家具体化,也是为了确认只有个体才是决策者这一事实。同时,他把那些要么强调国家是一个行政和强制体系、要么强调国家是公共机构的无效的国家概念加以分开。但是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应该把国家严肃地视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实体的原因,也就相当的不明确了。
从类似这些研究可以得出的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民族国家构成了爆发政治冲突的场所,但是在行动者与发生场所之间有巨大的差别。在描述国内政治时把这两个词等量齐观的做法必将带来一个主要的、无法解决的把国家具体化的问题。当今对国家中心主义研究的着迷不仅仅表明这是他们要给国家贴上一个没有明确经验意义标签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牢记国家中心主义研究并不新颖这一点十分重要。确实,直到五十年代,这种研究一直居于政治分析的核心地位。早期研究的失败既是因为研究过于规范所致,也是因为他们不能确定国家到底是什么所致。例如,早在六十年前,萨拜因(Sabine,1934,p329)就抱怨说,总体上来看,国家一词定义得非常糟糕。他特别指出“国家一词常强调政治组织这一事实使得要在国家和政府之间划出明确界线尤其困难”。我并不是指出最近的研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并且认为应该放弃这一主张的第一人。让我们看看伊斯顿的结论:
如果要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深入国家当中,那么就更应该说它已经被非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利用。最近几年,国家又暗暗地重新进入了传统社会科学的词典里。在这一事情上,即使仅仅因为我们没有对这一在社会科学里为人习惯了的新词语进行细致的考察,对这一术语的偶然接纳也搞得整个研究混乱不堪。不幸的是,也许因为国家研究在政治科学里头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易于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知道国家这一概念的真实内涵。事实上,“国家”这一词语的兴衰史——尤其是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里对这一词语加以抛弃,证明了它的意思的模糊性和操作的困难性。我对普兰查斯在他的艰巨而又复杂的理论事业里对这一问题的明确处理的分析研究看来证明了这一历史教训(Easton,1981,p321)。
伊斯顿对当今国家主义著作的批判是详尽的,也是很有力量的。然而此后的一些学者对他提出的问题既没有作出反应也没有加以解决。
最后,当代的一些学者试图回避对国家的一般性讨论,来对国家力量问题进行研究。在这样一种分析研究里,克拉斯勒(Krasner,1978)认为如果与日本政府相比,美国政府对内是软弱的,这一软弱对美国的国际国内经济政策的实质内容和实施都有很大的影响。然而,要就这一影响具体牵涉到哪些方面进行准确的估计非常困难。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克拉斯勒好象给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国家主义的解释说明,然而他的文章里交替使用“国家”和“政治体系”这两个词,这看来又似乎表明他很少看到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实际差别。
象克拉斯勒所使用的一样,国家力量看似指的是在对国内政策目标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之间达成共识(Consensus)和一致的程度。在日本,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共识看似更为彻底和全面,但是最为明显的原因是一些利益问题(尤其是劳工的利益问题)没有列入议事日程 (Pempel,1978)。相反,说美国政府对内的国家力量更为低弱,是因为美国在国内政策目标上很少能达成共识,这制约了政府领导人调动资源和贯彻政策的能力。由于语言表述的不同,克拉斯勒认为美国国家力量的软弱是因为有更多需要协调的人口和团体。
卡增斯坦(Katzenstein)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认为工业化晚发国家(比如日本)的国家力量可能要比早期工业化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力量更为强大些,因为这两类国家有不同的特性:
早期的工业化国家的政党是从社会底层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政党之间的进一步的政治联盟关注的是政治参与而不是官僚机构的渗透。而在工业化晚发国家里,政党是从顶层贯彻实施政治决策的工具;政党之间的联合集中关注的是官僚机构的渗透而不是政治参与(Katzenstein,1978,p332)。
早期工业化国家的放任自由主义的传统归因于他们对参与的强调,而工业化晚发国家对渗透和政策实施的关注导致了一个更强的干预主义传统的形成。结果就是工业化晚发国家表现出对国家政策,尤其是对侧重长期发展目标和侧重积累的特殊政策享有更多的共识。反之,工业化早发国家对政策的长期目标很难达成强大的共识,而是侧重于短期政策和短期消费。这样,国家力量在公共政策里得到了体现。
在这之后,卡增斯坦修正了他的观点,认为国家能力至少有两个向度(dimension)。首先,国家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行动者,他在对奥地利和瑞士进行比较时得出结论说,在这一点上,因为奥地利的块头比瑞士大(根据公共消费和国家官僚机构的规模大小),所以它的国家能力也就比瑞士更强。其次,国家也可以被视为“政策网络”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奥地利和瑞士的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渗透都非常强大、深远。”(Katzenstein,1985,p236)。 卡增斯坦得出结论,认为对奥地利和瑞士的每一层次的分析,都只说对了它们情况的一半(Katzenstein ,1985,p248),这二者加起来才构成全部真理。
我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由于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一些原因,公共部门的规模并不能告诉我们多少有关政治能力的信息,卡增斯坦的更新的阐释模式也只是对“国家力量多少可以通过公共政策来加以体现”这一观点的简单的重申。即便如此,由于度量标准缺少明确的内涵,国家力量的定义仍不准确。我相信,这一定义的不准确是国家含义不只是指国家政治舞台(政治冲突发生和解决的政治舞台)这一事实的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对国家一词的定义宽松泛化,必定导致国家力量一词定义的模糊性。
有些人相信国家定义的宽松化要比特指的定义更为有用,并进而声称对国家的准确定义必定是做作的、草率的、肤浅的。于是,爱文斯(Evans)和他的同事得出结论说,国家能力在任何真实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从这一问题到另一问题、从这一时期到另一时期都在发生变化,复杂而又具有辩证色彩,充满着矛盾和悖论:
事实给我们深刻地指出,我们不应该以一个普遍化、一般化了的连续谱的标准来简单地说某个国家的力量和能力是强的或弱的、或者是更强的或更弱的……我们不可能由在总体层次上一般化了的国家能力或国家力量来推论国家采取特有形式来干预实行的可能性。要能使自己的研究更为人接受,他在研究中就必须对那些与过去的国家政策制订、与国家行动的国内国际背景、而且彼此之间也密切相关的、现实的国家机构进行深入的调查和探究(Evans,Rueschemeyer,and Skocpol,1985,p352—53)。
这一论述暗示我们不应对国家政治能力进行一般性的定义,否则我们将适得其反。它还进一步暗示我们采用更严格的概念就是否认国家力量随时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但这些暗示将使我们误入歧途。
爱文斯和他的同事们对国家力量的分析方法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实质上,他们是要主张民族国家的能力没有多少共同本质。相反,国家力量由情势决定,并且呈现出一个连续的波动状态,因此他们认为通过考察特定的环境和背景、通过避免一般化,我们可以对国家力量认识更清楚、更全面。 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我相信,由于方法论的原因,这未必就是一个精确的、严格的分析。但理解到这并不只是在讽刺这一点非常重要。
克拉斯勒在对国家进行全面考察中,得出结论说,当今对国家的研究代表了一场告别六十年代盛行一时的行为主义的范式转变。他在对这一点进行解释时,对达尔(Darl,1961)的权力的多元主义研究和新近对国家权力的研究进行了比较。我们可以从他的比较中得到什么呢?按照克拉斯勒所说的,多元主义研究视角过于强调个人主义色彩。相反,新近的研究强调的“国家权力、包括一般性的政治信仰等制度性规则和制度性限制等等在达尔的图式里并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Krasner,1984,p227)。很明显,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路径解读达尔的思想。
《谁来统治》(Who Governs?)一书的基本结论认为要对权力作出一般性的论述、或者要清晰界定谁是权力精英,这非常困难。相反,对达尔和他的同事(例如Polsby,1980)而言,在提出对权力实施的更为普遍的见解前,他们认为考察不同背景和历史环境中的特定的问题非常关键。一旦这样做,权力实施由情势决定就变得非常明确,而且不同的行为主体的权力要依靠身边的政策议题和历史条件来决定。达尔是通过指出领袖和公民关系得以形成并因而制约权力实施的这一相互依存和变动的复杂过程,来作出这一结论的(Darl,1961,p325)。
我们来把这一观点与更近出现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要探讨国家力量…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对那些考虑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零和博弈和复杂的互动过程的观点进行彻底的辩证的分析”( Evans,Rueschemeyer,and Skocpol,1985,p355)——作个比较。新国家主义的这种分析的新鲜感比现实生活中的国家主义的新鲜感更为明显。确实,那种分析比它的支持者承认的观点历史更为悠久一些。
第三部分 近期关于国家和政治能力的研究第16节 小结
上述表明,当今的一些关于国家问题的学术著作在分析政治能力时的效用是有限的。首先,那些研究使用公共部门的规模来作为国家力量的标准,并因而遇到了严重的实际问题和概念上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著作对于如何区分公共部门和私域并不清楚。但是这些研究明显代表了从一般意义上界定国家力量定义的认真的尝试,这是它们的优点和长处。
相反,另一研究视角既否认国家力量的一般性定义的价值也否认它的可行性。除了认为民族国家是国家政治舞台这点可取之外,这一视角的模糊性是不可接受的。当把这一视角运用到国家政治能力问题的研究中时,它将给除了类似路易十四和博卡萨(Jean-Bedel Bokassa)之外的所有人带来使他们不知所措的具体化的问题。不过这一研究视角的基本困难还在于它的模糊性。明确界定国家定义的失败,使人回想起早期著作中在区分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和政治体制(regime)——它们都源于政治权威(Easton,1965)——时遇到的困难。探讨国家自治问题遇到的难题与早期著作中区分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和它的更宽的外界环境(enviroment)遇到的难题没有多大差别。在这些试图使研究变得更为具体的例子中,国家主义视角只不过是在早期的研究和争论上再贴上一个标签。阿尔蒙德告诉我们:“很难明白《把国家带回》(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一书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的启发和新的研究计划”(1987,p477)。 从方法论的更深的意义上说,当今关于国家问题研究的大多数著作事实上是在否认一般性定义的可能性,甚至于否定它的价值。
我相信我们能比这走得更远些。在国际舞台上,很明显,由于一些国家拥有更为丰富的资源(包括人口和工业能力),它们比其他的一些国家更具影响力。即便能力的标准有些不同,人们也容易以类似的眼光来看待国内政治能力问题。从表面上看来,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从政治意义上来讲相对发达,对它们而言,国家制度崩溃的事情更为鲜见——尽管魏玛德国和程度更轻一点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要排除在外。相反,自1975年以来黎巴嫩的国家政治能力就一直在微不足道和丧失殆尽中徘徊不定,同时,在黎巴嫩,政变、革命、动乱等等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了它的政治制度的脆弱性。这样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准确评估脆弱性的程度。
第四部分 制度和政治能力第17节 马克斯·韦伯论组织
没有任何事情比造就一代雄主更为难于操纵,更为难于成功,也更为危机四伏。
——马基雅弗利,《君主论》
象人们预言的一样,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革命前后十年的变化比任何一个十年的变化都要大。此后,变化又日渐缓慢下来,不是因为事情很少发生,而是因为事情很少第一次发生。
——克利夫特·吉尔茨,《民族的判定》
我早已简要地强调过制度对于政治能力的中心地位。现在我要就制度对政治能力有何影响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尽管从现代国家的角度来考虑,涉及到的政治问题是本世纪特有的问题,我的目标是要确定一个政治能力的一般型态。这意味着尽管政治能力与其说和政府形式有关不如说是与政府的规模有关,但我们还是不能完全回避政府形式的问题,因为政府形式与我们的基本分析单位——即杰克逊(Jackson,1982a)和罗斯伯格(Rosberg)所指的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密切相关。如果这一点得到承认,那么国家政治能力一般型态的问题(基于关注的焦点是二十世纪的政治这一理解),制度是贴上自由民主的标签还是贴上极权政治的标签,抑或是贴上教旨主义的标签问题,这些问题都不重要。后一区分(指政治制度的种类)只是说明了现代国家可以或试图建构的制度有不同的形式,对政治制度的效率并没有内在的影响。
政府规模是一个相关的“量”的问题,这一观点并不新奇。毕竟,阿尔蒙德(1960)和科尔曼(Coleman)的著作、亨廷顿的著作(1968)都曾试图确立一个根本上适用于所有现代国家的国家政治发展的一般模式。对政府效率的强调表明,政治能力问题最好应该当作一个组织创建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来加以探讨。
在马克斯·韦伯的经典性的分析中(1947),他认为规则是组织的核心,按他的术语来讲,就是社会“秩序”。尽管组织牵涉到行为的规律性或“社会行动的规范化”问题,但是组织的内涵并不这么简单。组织由深深植根于一套规则中的规律性和稳定性组成。在行为者认可了这些规则的价值这一意义上说,组织是有效率的。韦伯得出结论说,当大多数行动者认可了规则的价值时,社会秩序可以说是具有合法性的。
韦伯进一步认为,组织的合法性可以以两个途径来维持。首先是惯例和习惯,其次是法律:
对特定社会团体的偏差行为能作出整体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反对的反应,规则体系也因此得到保障,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一规则体系就可以称之为惯例(convention)。当遵守和服从得到维护——通过对偏差行为的肉体和精神惩罚,以强迫人们遵守和服从,并由被赋予了权力来承担这一功能的组织负责实施——时,这一规则就可以称之为法律(Weber,1947,p127)。
韦伯的分析与政治能力的问题关系尤为紧密。我在第二章中已经论述过,由于政治权力的相关性、依存性(relational),它与政治暴力有着较大的差别。然而权力最终要借助暴力(最少是含蓄的暴力威胁)来维持,暴力的运用又引起权力的损失。当权力被广泛视为具有合法性的时候,权力的实施也要容易些。在这种情况下,包含了对违规行为实施惩罚的法律同时制约着各个组织,但是,如果人们把那些法律视为合理的“惯例和习惯”,法律也就更为有效。然后,在惯例得到法律的支持的前提下,政治组织把规则内化为惯例和习惯。
这样,国家政治能力指的就是国家的法律秩序和规则为人接受和认可的程度。韦伯的分析也就与法律秩序和规则如何为人认可和接受紧密相关。众所周知,韦伯指出了三种权威型态:合理合法权威;传统权威;克里斯玛(charisma,又译为个人魅力)型权威。现在我们来逐个对它们进行分析。
合理合法权威由一般化了的规则构成。这些规则是普遍的、非个人化、非人格化的,它适用于所有相关的人(在当今的背景下,是民族国家的所有公民)。这一权威为组织化了的行政人员构成的官僚结构体系覆盖着。
传统权威不是源于明确的规范化了的规则,更主要的是源于对传统价值观念的亲附、情感和忠诚。因为人们总是这样忠诚于传统价值观念,权威也就被认为是必须遵守和服从的。在运用传统权威时,规则不必是非人格化和普遍化的。确实,韦伯把传统权威看作是“最原始的权威类型”(1947,p131)。
尽管在传统权威和合理合法权威型态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就我们看来,注意到这二者之间的基本的共同点更为重要,那就是,它们都不能被迅速地创造、形成或强加于别人身上。它的特性决定了传统权威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至少它的臣民们要能在这一时期内相信这一权威一直存在着——才得以形成。 同样,合理合法权威也要经历一段时间才得以形成,尽管韦伯把它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即使冒险地假设,目前在所谓的工业民主国家里这一权威型态非常明显地普遍存在,这些国家的宪政秩序也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建构起来的。 相反,它们是经历了一个困难重重的漫长过程才得以形成的,在这一过程里,政治领域的范围通过两条途径才得以扩大。首先,公民权利日趋普遍化:尽管这一进程总是充满了不情愿的妥协,公民权利才扩大了多伊奇(Deutsch,1961)所称的“政治上的相关阶层”的规模。第二,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意义上来说,政府的范围也同时得到扩大。就我们看来,韦伯在对合理合法权威和传统权威进行探讨时所揭示出来的演化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演化过程强调了发展所经历的时间。
个人魅力(克里斯玛)型权威与前面两种权威完全不同。在韦伯看来,领袖拥有个人魅力,他居于由一帮信徒和追随者构成的圈子和集团的中心,并被他们包围着。这些人是革命领袖,他们对权威的渴望和要求势必与制度化了的权力现状发生冲突:
克里斯玛权威否定过去,在这一意义上它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这种权威不是根据财产占有的多少来分享相应的权力地位,也不是因为某个人是首领或某个集团是一个拥有特权的集团就享有这种权威。他们合法性的唯一的基础是个人魅力,就如事实所表明的一样。即是说,只要他能为人认可并能够使他的追随者和信徒们满意,他就拥有这种权威。但这种权威只有在人们对领袖的个人魅力保持信服的情况下才能持续下去(Weber,1947,p362)。
因为个人魅力型权威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因此韦伯把这种权威看作政治变迁的主要基础。成功的克里斯玛型权威的革命运动能削弱既存秩序的合法性,不管这种合法性是建构在合理合法基础权威上还是传统权威的基础上。
韦伯在自己的分析中充满了大量的历史事例,从中国的专制君主到摩门教的建构者——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 近期的政治史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大量的例子。比如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古巴的卡斯特罗、伊朗的霍梅尼。如果我们把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革命领袖也包括在内,那么这一名单将迅速地扩大。最著名的克里斯玛型民族运动的领袖包括印度的尼赫鲁、越南的胡志明、埃及的纳赛尔、加纳的恩克鲁玛、肯尼亚的肯雅塔和坦桑尼亚的尼雷尔。
韦伯对克里斯玛型权威的分析是重要的,因为它使我们对政治秩序变迁或推翻的方式有所关注。这种集中关注明显与政治能力问题密切相关,因为政治秩序土崩瓦解了,正如本世纪发生的主要的革命——欧洲殖民帝国的崩溃、和前苏联的解体——一样。
但是韦伯的克里斯玛型权威这一概念还可做进一步的引申。人们关注的是过去三十年“新”国家出现的问题。推翻现存秩序是一回事,用一个新的秩序取而代之又是另一回事。韦伯认为,个人魅力是个体的,在某种程度上“尤其与平常的制度化的组织结构显得格格不入”(1947,p363)。这就是它之所以是革命性力量的原因。但一旦旧秩序被推翻,革命运动取得成功,而且这一进程包含着一个根本的转型,那么克里斯玛型权威本身也将被“制度化、程序化”。但是,个人魅力只能为克里斯玛型权威提供一个片刻的、短暂的生存基础:
纯粹的克里斯玛型权威只能存在于它的产生阶段。它无法稳定的保留下去,它要么与传统权威结合,要么与合理合法权威结合,要么二者同时兼备(Weber,1947,p364)。
克里斯玛型权威的昙花一现意味着这种权威是一种不稳定的权威类型,它自身包含着自我覆灭的种子。
这种情况就象克里斯玛型领袖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样明显,当领袖们退休或“消失”了,他的追随者们面临着一个确定继承人的问题,这一问题非常明确地存在。那么,它的成员们又如何在新的社会秩序里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呢?韦伯的答案非常简单。首先,追随者(比如说,革命成员或民族主义运动的骨干)对延续他们的共同体有着物质的和理想的兴趣。其次,他们对维持他们的关系网络——也就是巩固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新的秩序——有着更强的兴趣:
不仅如此,他们对维护新秩序的兴趣源于他们对理想和物质的考虑,要把他们自己的地位建构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这首先意味着,他们要把这一切变得可能:加入到正式的家庭关系网络里,或至少是通过恢复已经被普遍割断联系的追随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和家庭关系来享受一种稳定的社会地位(Weber,1947,p364)。
换言之,新运动的成员会寻求程序化并因而改变克里斯玛权威的实质,因为他们受到谋求权力和职位和安全保障(1947,p370)考虑的驱使。这种观点后来被米歇尔斯(Michels,1958,1927)扩展并表述为“寡头统治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其实这并不偶然(see e.g.,Mommsen,1989,chap.6),因为米歇尔斯曾经一度是韦伯的学生。
我已经指出过制度化的过程始自旧秩序的摧毁。然而,克里斯玛型领袖
退出政治舞台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只有他们退出政治舞台,任何个人权威遗留的残余才能彻底驱除,这样,他的后继者们就无法依赖这种权威来推进自己的目标。在那个过程里如果新秩序的程序化运动没有成功,那也就说明克里斯玛型领袖没有能够退出政治舞台,个人权威的残余还得以留存。当然,这并不是说程序化通过领导权力的转移已经成功实现了。但是权力继承是地位巩固的关键,因为“在权力继承中,领导人和他要求的合法性的性质都已经发生改变”(Weber,1947,p371)。
那么权力的继承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呢?韦伯认为权力继承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但是最重要的形式是,继承人通过指定的(或者经由第一人领导人的指定或者经由他的追随者的指定)方式和世袭(世袭者也要具有个人魅力)方式产生。鉴于1945年后印度的历史和印度独立后尼赫鲁—甘地皇朝在印度政治中所起的作用,韦伯把印度当成了权力世袭的经典案例,这至少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在此转移话题。有几位学者认为韦伯关于克里斯玛型领袖的探讨是模糊的(例如,Friedrich,1961;Blau,1963;Ratnam,1964),确实,这些指责有很多充足的理由。 例如韦伯把教皇职位的继承当作由领袖追随者在其中指定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为继承人的例子(Weber,1947,p371),这也就意味着教皇继续依靠个人魅力作为权威的源泉。在这一学派里,近来有更多的学者认为个人魅力常常可以被当作权力延续的基础来发挥作用(例如Anderson,1972;Willner,1984)。
韦伯更为根本的观点是,个人魅力只能被现有秩序的挑战者当作权力的短暂的基础来发挥作用,而上面的这些主张却混淆了韦伯的这一观点。一旦旧有的秩序被新的秩序所取代,权力的挑战者就必须面临把自己的权威制度化的任务。不错,如果有这么一个能提供一个他的工作人员得以正常运转的个人框架的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那么这一目标比较容易达到。但这只是掩盖了克里斯玛型权威短暂性的本质。把教皇权威看作个人魅力符合罗马教廷的利益(这也是它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教皇权威已经高度制度化这一事实。与此相似,在现代印度政治中直到近期才停止的突出的家族政治,也不能掩盖印度政治制度的连续性和程序化这一事实。
韦伯对领导权力继承重要性的强调对政治发展或制度化的问题有着直接和明显的影响。当人们考察革命后的巩固和制度建设的进程时,领导权力继承问题的重要性就变得非常清楚。同样,人们在思考非殖民化后的新兴国家的政治事件时,这一问题也相当重要。在对新的制度性秩序的成功前景进行分析时,对权力继承问题的关注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在卡斯特罗去世后,古巴人民是否原意坚持当前的政治形式?很明显,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最终没有能够维持他创建的政治形式。在霍梅尼死后的伊朗,现有的政体的远景又当如何呢?难道坦桑尼亚的政治安排将能够挽救尼雷尔创建的体制?
从整体的层次上讲,韦伯对克里斯玛型权威的探讨又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发展的时间(timing)问题。我已经指出,韦伯的合理合法型权威和传统权威的一个基本的特性是这种权威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创建。这说明国家政治制度的实际年龄(chronological ages)是测量这些权威类型效用的一个主要标尺。同样,克里斯玛权威这一概念也使我们必须关注新秩序下的领导权力继承和制度建设的问题,鉴于新兴民族国家的绝对数字,这一问题关系非常。考虑到制度的代际更替年龄(generational age),这一问题也驱使我们回到发展时间问题上来。
所有这些说明组织年龄有两个组成部分:实际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韦伯的分析至今仍然是对这一问题的经典论述,它对当今的学者在研究组织的更新倾向(liability of newness)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tinchcombe,1965)。那么这些研究对分析政治能力有何启示呢?
第四部分 制度和政治能力第18节 组织实际年龄
斯塔巴克(Starbuck,1965,p451)在他的著作中把组织发展定义为“组织年龄时间范围内的变化”。把发展等同于实际年龄,这是建构在组织生存下去的可能性随它的年龄的增加而增加、手边的经验事实总是确定的和有效的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比如在美国,寿命达五十年以上的商业公司只占最初公司建构数目的2%。与此相似,美国的产业公会年龄达五十年以上的只占最初建构数字的4%(Starbuck,1983)。如果把年龄越长生存能力越大的观点考虑进去,那么这些情景与组织具有自我更新倾向的观点是完全吻合的。
我并不是说存在着这样一个神秘的临界点,达到了这一临界点,组织就将永远生存下去。斯塔巴克在报告中指出年龄达五十年的公司有30%在其后的十年里就不存在了。美国产业公会的相关数字是26%(Starbuck,1983)。认为组织具有自我更新倾向的人更加含蓄地断言,组织生存的可能性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换句话说,对年龄较长的组织而言,组织死亡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了(但很难完全消除)。这告诉我们发展总是一个程度的问题,组织永远保留着一定的脆弱性。
斯塔巴克是从行为调适性的角度来对这一经验规律进行解释的(1965)。成功的组织是那些在早先就显示出对外界环境具有极高调适能力并因而在将来可望继续具备相当的调适能力的组织。仅仅因为调适包含组织的定型(formalization)和学习(learning),年龄就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因为有效化和学习都需要时间。
组织的定型模式很容易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为的一般模式得到稳定。一旦个人和组织的角色被固定下来,规范的运作程序也就随之出现。年龄是这一程序的核心,这不证自明,比如,组织规范的运作程序的观点就预设了组织连续性的存在。尽管毫无疑问,早期有效化的现象是最为激动人心的(1965,p478),但斯塔巴克仍然认为组织的有效性应该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因为定型是一个学习和调适的过程。
我们应该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组织定型化的过程说明了组织正在变得更加理性起来。相反,定型化只是简单地表明了惯例化(routines)的创建和出现。正如斯塔巴克指出的那样,
年轻的组织缺乏区分重要问题和非重要问题的经验,也很少有处理日常问题的机制…而历史更为悠久的一些组织已经学会了忽略次要问题的本领,而且处理日常问题的机制也已积累起来(1965,p481)。
换言之,假定环境是相对稳定的,那么随组织年龄的增长,组织将形成一个集体性的记忆(Walsh,Ungson,1991)。这将为组织提供一整套组成技巧的惯例(Nelson,Winter,1982,p124)。惯例(routine)既是组织日常运作的根本要素,也是处理新问题的关键。没有这些惯例,很难把问题定性为“新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组织革新可以看作是既有惯例的新的组合(Nelson,Winter,1982,p130)。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惯例成了组织实现、完成自己的目标的根本所在。
组织的目标是什么呢?从一定层次上来说,这一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一般而言,组织声明的目标多种多样,并不清晰的组织意图也可能一样的千姿百态。而且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也看来取决于我们提出这一问题的层次。比如说,组织内部的不同部门可能有自己唯一的目标(就这一问题,请参Perrow,1968;Simon,1976,chap.12)。
如果我们在另一层次上考虑这一问题,它也就变得更容易处理些。组织表明的多样的目标都建构在组织生存这一假设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来说,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获取利润,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为了表达会员的利益,其它的团体的存在可能要表明自己甚至更高的目标。但在任何情况下,一个组织都不可能是完全富有效率的,除非它处理好确保自己生存下去的更为根本的问题。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年龄的增加,组织目标也会得到相应的增加,组织生存能力也得到增加,这种情况非常明显,因为老的组织更具弹性。西蒙(Simon)指出,组织吸引了一些人,因为人们发现组织声明的目标与自己的目标是一致的,另一些人是为组织本身的特色所吸引。
忠诚于组织目标和宗旨的个人,将抵制对目标和宗旨的修正,如果目标和宗旨变化太快,他们甚至可能拒绝参加这一组织。忠诚于组织的个人,将支持可以推动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组织的机会主义的变化(Simon,1976,p118)。
处于成长期的组织倾向于由第一类人构成,这是明显的事实。但是斯塔巴克(1965,p473-477)认为由于三个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类人将在组织中发挥支配性的作用。第一,随着组织年龄的增加,组织的结构形成了,组织中的个人和团体与特定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第二,组织中的关键人物将花很大的精力去推动人们对组织的价值忠诚。第三,那些与组织关联最为紧密的人也是那些最有可能在组织决策和行政事务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人,借助这一地位他们可以对日常事务施加相当的影响。
鉴于这些情况,老的组织避免了组织更新倾向并更有可能继续生存下去。不管我们把这种行为说成是灵活、有弹性还是机会主义,这都没有关系。更为重要的地方在于,那些居于关键位置的人,有着通过种种手段来无限地延长制度的寿命的动机。韦伯主义对这一问题的根源上的探讨是相当有趣的。韦伯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如果要使这种权威关系更为持久一些,就需要把它惯例化和制度化,否则它就只是昙花一现。他进一步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运动的成员使权威制度化和惯例化,这由维持他们自己创建的新秩序的物质利益所驱动。
我已经强调过,组织生存可能性随组织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的观点,这是建构在随时间的推移,组织对环境会变得更有调适性这一假设的基础上。这一过程进一步假设,组织中处于关键地位的人将与组织生存问题关系日益密切,并受组织生存问题驱动、影响和左右。尽管这一观点适用于各种情况,但它与政治组织的关系看来特别紧密。
当我们对企业进行考察时,这一标准就变得异常清晰了。企业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利润的最大化——企业的生存事实上取决于可获利性。可获利性是一个我们易于把它和数字联系在一起的量(这一联系忽略了诸如短期行为和长期行为之间的重大差别)。相反,政治组织不是获利性的组织,这意味着它们的绩效不能以直接的经济标准来衡量。反之,它们与资源(它的内涵尚没确定)打交道,因此必须用社会和政治标准来衡量它们的效率。政治组织是在一个因果关系信息极度缺乏的环境中来使用模糊的技术手段(e.g.,Edelman,1964;Thompson,1967;March and Olsen,1976)。因此,效率的明确度也就比较低。
在这一通过不确定的社会和政治标准来判断成就的背景中,因为生存这一目标的明确性,生存特别容易被看作组织的准确目标。这一点在施莱辛格(Schlesinger,1991)对竞争性政党行为进行分析的著作中论述得非常清楚。但在其他的政治环境中也同样适用。例如,贝茨(Bates,1981,p5-6)在对非洲的农业政策进行评估时就假定,“总体上来说,(农业)政策就被用来确保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用来平息影响重大的政治暴力,用来加强政治体制维持权力的能力”。此后,阿姆兹(Ames,1987)表明,要根据拉丁美洲的主要的政治执行机构的生存压力(而且这些压力影响到公民行政和军事行政等多种行政活动)来理解它们的公共消费的模式。政治关注的是如何估算(在极度不确定的条件下)那些最有可能吸引支持者并确保行政当局继续执政的政策成分比例。
生存目标作为组织支配性的目标的突出性看来不可抗拒。正如米格代尔在对第三世界政治进行观察时所指出的,
如果政治议程的发起者没能度过政治风险并生存下去,那么任何政治动议都没有意义。在政治上生存下去是取得任何长远的、意义深远的社会变化的前提条件。它成为国家领导人关注的主要问题。社会变迁计划可能仍是公共辞令的基础,它还甚至是政策声明和司法的基础,但是,在国家的顶端,谋求政治生存的政治使国家机构彻底完成这一计划的能力丧失殆尽(Migdal,1987,p418)。
米格代尔对生存目标重要性的强调非常准确,但他进一步认为生存政治削弱了政治能力,这却很难让人信服。组织中的关键部分与这一生存问题日趋相关,因为惯例化、制度化的形成产生是政治活动的体现,而不是原则上代替机会主义的体现。确实,因为没有别的明确的、可供替代的、可行的绩效标准,连续性就假设了自己作为评估政治组织绩效的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我早先提到了斯塔巴克(1965)根据组织实际年龄的标准来界定组织的发展。国家政治能力有效的测度方法包含的远远不止这些。但是,我刚刚考虑的这一角度表明实际年龄是政治能力的关键的组成部分。 这一点在早期关于政治发展尤其是关于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的著作中得到了确认。比如说,西尔斯(Shils,1963)就把新兴国家主权的“新(recency)”与问题的严重性联系在一起。他还认为尽管老一些的第三世界国家问题重重,但它们有着自己可以依凭的政治传统和官僚体制的传统。反之,新兴国家甚至连这些可以凭依的传统也缺乏。杰克逊(Jackson)和罗斯伯格(Rosberg)在对次撒哈拉非洲国家的总体脆弱性的分析中也持这种观点(1982a)。韦纳(Weiner,1987,p41)也对这点加以强调,他说,与非洲国家相比,在沦为殖民地前,亚洲和中东国家有着一段官僚制度得到良好建构的悠久历史…当今的亚洲国家可能和非洲一些国家同样专制独裁,但它们却更有效率。鉴于次撒哈拉非洲国家非殖民化的“新”,这些观点也与我对实际年龄的强调完全一致和吻合。
第四部分 制度和政治能力第19节 组织代际更替年龄(1)
除了对实际年龄进行考察外,我们还需对代际更替年龄进行考察。代际更替年龄是指政治秩序中占据最高领导位置的个人的数字。在情况的一端,领袖既是新的政治秩序建构者,也是新秩序的化身。在情况的另一端,领袖继任模式已经高度制度化、惯例化,新的政治秩序也已经历了几代的延续。这意味着在这个国家里已经形成了政治秩序独立于(不依附于)执政群体和个人这样一种广泛的认同。实际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彼此密切相关。实际年龄短的制度,它的代际更替年龄也同样短。不过,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这一区别对国家政治能力问题特别有影响。
最明显的是,实际年龄指的是制度的年龄。当我们把它运用到现代民族国家里时,我们关注的对象就成了诸如国家制度形式或国家官僚体制的年龄等等的现象。相反,代际更替年龄集中关注的是领袖个人而非制度。它是这样一种思想,它把我们引向韦伯在对克里斯玛型权威的制度化、惯例化加以讨论时提出的问题,这样我们能判定在特定环境中的政治权威的首要基础是制度还是个人。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对早先(特别是第一代领导人和新秩序的建构者)的领导人来讲,政治权威是否应建构在一个非个人、非人格化的基础上,这一问题很难判断。这构成更新倾向的另一个方面,而且在对政治制度的长期生存能力进行分析时,它有助于引起对领导继承现象总体上、全局上的关注。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毛泽东。他是本世纪主要的政治领袖之一。他的领袖地位在1949年前的革命中就已经确定下来(通过诸如长征之类的事件),以致他在1949年后成了中国革命建构的新秩序的化身。他产生的影响的程度是那么深远,以致在他生命的晚期,有许多政治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毛后的中国将是什么样子?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完全源于毛的个人领导在后革命中国的明确的中心地位。例如,对毛泽东思想(Maoist)的顶礼膜拜表明他个人成了新政治秩序的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以致毛泽东思想和新的政治秩序二者不可分离。那么问题就成了随着毛明显的支配性的个人色彩的消失,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现代政治史充满着这种事例。一般来说,作为民族运动的政治领袖,在非殖民化运动后,他们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他们的领袖地位在独立斗争中就被广泛地认可了,而且许多情况下(比如加纳的恩克鲁玛,肯尼亚的肯雅塔),他们曾被殖民势力监禁过。因为他们在非殖民化运动中的显著地位,他们个人的领导地位也就为新建构的国家所认可。
这就是在新的政治秩序中个人领袖地位的情况。这种情况与国家政治能力问题的关联性源于新政治秩序的不健全、不成熟和不稳定的事实。在这些背景中,政治领袖手边的紧要任务就是通过合作或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来巩固他们的地位。由于新秩序的不稳定性,他们巩固自身地位的努力是冒有风险的,而且极有可能失败。应该肯定的一点是,短期看来,毛泽东和肯雅塔取得了成功。但是即便从短期看,恩克鲁玛明显地失败了。
说代际更替年龄是国家政治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建构在新政治秩序制度化的困难这一假设的基础上。这一观点把韦伯的“克里斯玛型权威是一种个人权威形式,它注定脆弱不堪、来去匆匆”这一观点视为公理。这一观点因而假定,克里斯玛型领袖及他的追随者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的权威制度化,但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艰巨而又可怕的任务。
我是在政治意义上使用克里斯玛权威这一概念,它与当今其他人对这一概念的运用有所不同。这一概念的一般的用法更忠实于韦伯著作中的字面意义,但并没有抓住韦伯使用这一概念的实质和精神。我早已指出,这种观点因为自身的模棱两可性而遭到批评(e.g.,Friedrich,1961;Blau,1963;Ratnam,1964),对这些人在进行批评时也没有对它作出过修正。特别的是,韦伯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有着心理的和社会的根源,而且在韦伯看来心理根源比社会根源更为重要。此外,韦伯使用这一概念的部分意图是要对克里斯玛型权威和合理合法型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进行比较。
我们应该承认,克里斯玛型权威总体上是在心理意义上来认识的,而且被根本上认为是非理性的。例如,得克米延(Dekmejian)和威左米尔斯基(Wyszomirski,1972)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的实施导致了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互动,这一互动需要急剧的社会危机、典范型人物和价值转型这些情况的存在。在某一层次上,这看似合理,但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它们包含什么意思。他们是这样界定危机情势(crisis situation)的:
既存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的崩溃引起社会的病态反应。在这段时间内,非理性的、精神分裂似的心理迷茫出现了,它们使人们产生严重的心理依赖感,人们的期望也被提升。在政治层次上,合法性危机危及到政治体系、它的领袖、意识形态和制度。盛行一时的大众异化、社会分裂和认同危机使得百姓易受大众鼓动的影响(Dekmejian 和Wyszomirski,1972,p195)。
那么什么样的领袖才是克里斯玛型领袖呢?
他是…一个倾向于冒险的革命者。作为他所处的充满危机的环境的产物,他是一个被严重异化了的个体。通常他的异化可以追溯到他不稳定的家庭生活和他在社会上经历的失败与痛苦——也就是说,他不能进入上层社会,还有他经历过监禁生涯,有着认同危机,这些都是驱使他采取革命行动的因素。他要么把自己引向其他异化,要么最终成为把那些被异化了的大众包容进来——这是他的运动所追求的目标——的扩大的社会阶层的核心。在这一意义上,他是一个社会阶层的边缘人(marginal)。(1972,p196)
在这样一个领袖能利用危机局势的地方,克里斯玛权威才得到了实施和运用:
克里斯玛型权威的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在领袖和他的追随者之间有着一种精神上的关系。在领袖权威性价值的纽带作用下,克里斯玛关系使领袖和他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团结,形成了坚强的精神联盟。在这一环境中,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执行某种心理功能,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他先天就扮演一个“值得信赖的代表”的角色。而且,他赋予他的信任者一种舒适感、慰藉感和归属感(1972,p197)。
得克米延和威左米尔斯基观点的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他们坚持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从根本上说是非理性的、神秘的。克里斯玛型领袖被当成救世主式的人物。当然,对神秘性和非理性的强调与韦伯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确实,对克里斯玛权威的神秘性的强调,成了现在研究个人崇拜现象的关键的组成部分。
比如说,威尔纳(Willner)就把克里斯玛型领袖界定为领袖和追随者之间具有如下特点的一种关系:
1、领袖多少被他的追随者想象成一个超人。
2、追随者盲目地相信领袖的声明。
3、追随者无条件地服从领袖下达的行动命令。
4、追随者对领袖绝对地、恳切地支持和献身(Willner,1984,p8)。
而且,对领袖超人品质、对领袖的盲目的无条件的忠诚、对领袖无条件地献身与支持的强调,都充分说明了这种现象的所谓的非理性特征。
然而这样看待问题将产生相反的结果,而且它使我们的注意力从到底什么是克里斯玛型权威的根本特征这一点上转移开了。把非理性引入政治研究的基本困难在于,它模糊了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基本的政治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克里斯玛这一词语也就只是变成了一个贬义形容词。把克里斯玛型人物想象成一个具有说服追随者——使他们相信自己具有在新秩序的建构中作为领袖必不可少的特殊的天赋——的高超的政治技巧的人物,比把克里斯玛型领袖当成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更为有用。而且,尽管所有的追随者都认可领袖具有特殊品质这非常重要,但没必要让所有潜在的追随者都信服这一点。
第四部分 制度和政治能力第20节 组织代际更替年龄(2)
对克里斯玛权威的心理因素和非理性的强调会造成太多的约束和限制,这一观点完全源于威尔纳的分析。例如,威尔纳就认为卡斯特罗、甘地、希特勒、墨索里尼、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苏加诺是完完全全的个人魅力型领袖。而凯末尔、列宁、毛泽东、纳赛尔、恩克鲁玛和庇隆只能算是“可能的个人魅力型领袖”或者“准克里斯玛型领袖”,因为他们并不具备足够的神秘色彩。让我们来看看她对列宁的分析:
列宁死后,关于他的个人魅力的神话是如此强大,以致出现了忽略这一事实的趋势:列宁在1917-1918年对他最亲密的追随者的反对意见随心所欲,这不是因为他的追随者对他的判断绝对信任,而是因为他的意志、思维的逻辑性和他威胁退出革命所带来的力量。与此相似,人们常常忘记在此期间他在彼得格勒百姓中的支持也是时增时减(Willner,1984,p39)。
威尔纳认为问题在于,人们有各种理由相信所谓的超人式的领袖也容易遭受到同一类型的压力——当然,她并没有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具体的结论。我们也不打算去寻找这一类的证据。例如,被认为是具有个人魅力型权威的甘地,正因为在伦敦印度问题会议之后印度国民议会拒绝完全采纳他的建议,他便于1934年退出印度国民议会。重申一点,克里斯玛型权威只是一个政治产物,而不是一种心理的或非理性的现象。
尽管韦伯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是心理因素的结果这很大程度上混淆了事实,但他的基本观点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只是社会剧变时期政治权威的短暂的基础——1917-1918年的俄国是最好的例子。在这样一段时期里,克里斯玛型领袖能够被当成是新秩序的有力的象征和化身,而且领袖本人也用革命的话语帮助建构这样一种认同。这种认同之所以非常关键,是因为他们能对尚未定形的政治形势产生模式化的影响,这一模式烙上了领袖的人格色彩。因为在政治剧变时期争夺权力的各种联合不断地分化组合,克里斯玛型领袖必须拥有维持自身地位的各种政治技巧。这些技巧包括通过自己坚强的意志和逻辑性思维的力量、通过包括威胁退出革命的种种策略来说服其他人的能力。实际上,退出革命的威胁成功地发挥了作用(正如威尔纳在分析列宁时所说明的那样),这点本身就说明了他的追随者承认这一领袖对革命起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正是对领袖的这种认识是克里斯玛型领袖权威的核心,而且用非理性的或神秘的词语来描述克里斯玛型权威将绝对地一无所获。
在另一相似的思路上,得克米延和威左米尔斯基把克里斯玛型领袖当成是一个有着万分痛苦的诸如监禁(因他的政治行为所致)经历的边缘化的异化人,他们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抓住问题的关键。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许多民族运动领袖能够从殖民政府对他的监禁中捞到政治好处。通过改变对他们的认识——把他们当成一个献身于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伟大事业(他们把这一伟大目标作为自己的化身)的殉难者,从而让监禁生涯来增加他们的政治地位。 在这一意义上,监禁不应该看成是一种肉体性的伤害,相反,它是一种有助于建构领袖政治魅力和权威的巨大力量。
如果把这一分析运用到政治能力上,克里斯玛型权威就是一种有着本质特性的、与其他权威根本不同的权威,因为它是一种个人的权威形式,也因为围绕新秩序建构和形成,它最有可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最大的问题是克里斯玛型权威是否总能被制度化。也就是说,克里斯玛型领袖是否能够运用自身的存在——他的存在象征着一个新秩序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新的政治组织能得到创建)?正如马基雅弗利和其他的许多人认识到的,制度化这一任务非常艰巨。此外,克里斯玛型权威制度化和惯例化的程度也难以抽象地度量。只有在领袖职位由下一任从克里斯玛型领袖个人手中继承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明白,新政治秩序如何制度化或者新秩序是否会演变成一个更加单调的个人统治制度这点的真正意义。这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大家对领袖的继承问题会有着广泛的兴趣(e.g.,Burling,1974;Calvert,1987)。
即便克里斯玛型权威能够有效地用来建构新的政治组织,第一届领袖的继承也可能是动摇不定的。但是,在一个“成功孕育成功”(success-breeds-success)的机制下,随着时间的流逝,领袖职位由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过程将变得日益可以预见。换句话说,尽管第一次继承可能多少有点令人痛苦和难忘,但是日后的继承过程将因为制度化和惯例而变得更加容易。杰克逊和罗斯伯格(Jackson and Rosberg,1982b,p21-22)认为在作为法律实体的历史更为悠久的国家(比如本世纪革命之后的中国和俄国),更有可能出现这种结果(但远非必定如此),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国家层次上的既存的政治传统更多一些。相反,在作为法律实体的历史更为短暂一些的国家,比如在大多数次撒哈拉非洲国家,领袖继承可能仍然问题重重。
如果领袖职位继承的进程没有有效地制度化,那么,很明显,克里斯玛型权威没能用来建构牢固的政治制度。在那种情况下,最有可能出现领袖继承的个人化或世袭化局面(Zolberg,1966;Roth,1968 ;Jackson and Rosberg,1982b,1984b)。个人统治会遇到克里斯玛型权威统治的问题,甚至问题还不止这些,因为世袭统治者很少能显示自己具有类似于个人魅力的天赋的东西,并且很少声称自己具有特殊的政治使命。确实,正如希欧伯德(Theobold,1985,p555)所指出的,在特定的基础上,这种个人统治的一系列不断变化的任务和权力,都是由最高统治者来委派和确定的。在权限和固定薪水都没有明确界线的情况下,任职者和职位之间的分别也不可能明确。这方面的相关的例子包括许多军事政变中的来历不明的官员,或者也包括海地的杜瓦利埃父子。
当然,不管是否已经制度化,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应具备个人的政治技巧。然而世袭领袖职位却要特别些。在第三世界政治中,世袭统治包含有典型的被称为“庇护主义(clientlism)”的宗主-庇护(patron-client)关系现象,在这一现象中,领袖们被绑在一起,他们利用联合组织、追随者甚至利用敌人(就这一现象,请参Schmidt et al.1977 论文集)来相互支持和帮助。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结构可能会以类似于组成联盟(这种情况对于所有的政治活动来讲非常普遍,并不显得非常特别)的形态出现。但是它们的任何相似之处都比现实要显得明确些:
个人的宗主-庇护关系取决于关系模式中的个人,并且它无法象制度那样延续下去。尽管宗主-庇护关系的纽带体系能够超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生命和财产、地位而存在下去——就象制度所做的一样,尽管制度同样会受到个人权力和财产的严重影响,但这种宗主-庇护关系与政治制度有着很大的不同。统治者的改变…能够很大程度地改变既存的庇护关系模式以及与这种庇护关系模式缠结在一起的政治财产和政治地位状况(Jackson and Rosberg,1982b,p40)。
因为个人领袖职位最终要依赖个人而非制度,所以它天生就不稳定。在个人统治中,任何看似各得其所的机构实际上都是脆弱不堪的,因为这些机构被领袖们控制和占领着(Pye,1985,p23)。个人统治的显著特征在于领袖职位的改变,标志着组织代际更替年龄的钟表又拨回到了起点(或者至少倒退了许多),因为它缺乏一个能提供继承框架的机制。相反,它的领袖职位的改变是通过越出宪法的军事政变,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显示出来的(巴比·多各斯接任海地总统职位是因为他父亲在1971年逝世)。
所有这些都强调了制度的代际更替年龄对于国家政治能力的中心地位。至少从韦伯开始,有很多人强调:如果制度效率低下,就需要使它惯例化、程序化。由于克里斯玛型权威强调个人因素,这样,它与惯例化、程序化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在创建新秩序上,克里斯玛型权威最为重要,但这种权威生来就注定短命。当克里斯玛型权威演变成世袭性的统治时,刚刚形成的惯例和制度仍然保留有个人基础。代际更替年龄的意义源于制度化对于政治能力的中心地位和这一事实:它是一个把我们的学术注意力重新引向领袖职位继承过程的惯例化和制度化的东西。
第四部分 制度和政治能力第21节 小结
组织年龄对国家政治制度能力如何施加影响,这种施加影响的方式有何重要性,这都是我在本章中要强调的问题。我的分析是在总体上借用韦伯对组织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来展开的,同时我强调组织更新倾向的重要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秩序的建构和马基雅弗利所认为的完全一样的困难。我对这点的强调与对新兴国家政治发展研究中重申过的问题完全一致。尽管那些新兴国家与三十年前没有多大变化,但它们的相对年轻仍是它们最为显著的政治特色。
我探讨过制度年龄的两个组成部分——实际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当然,二者相互关联,尽管如此,可能还是会有人认为我们应该首先关注组织的实际年龄而不是首先关注代际更替年龄。然而,这样做将使我们失去很多。在我们去努力尝试度量制度的实际年龄时,与这种对组织代际更替年龄的内在兴趣一起,对代际更替年龄和继承过程的集中关注将有助于我们决定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在第六章中,我将回到这一问题。
最后,制度年龄问题不是一个能简单的用明确的直线性的标准来回答的问题。即是说,对国家之间的富有意义的比较观照,不能建立在政治年龄的简单的数字基础上,因为发展不是制度和组织年龄的直线形的延长。相反,这样看——在制度和秩序建立后的前几十年里,组织的更新倾向最为明显和重要,并且,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一更新倾向的意义将变得更小——倒看似更有一些道理。因此,两个制度年龄分别为一百年和两百年的国家的发展程度的差别,与两个制度年龄分别为十五年和三十年的国家的发展程度的差别相比,更不值一提。这一非直线性直接源于组织定形化的可调适、可修正的性质。尽管认为组织的制度化会随年龄而增长这是合理的,但牢记斯塔巴克所说的“最早的定形化表现也是最引人注目的表现”(Starbuck,1965,p478)也非常重要。这正如吉尔茨(Geertz,1977)指出的,前面的几年是决定性的、关键的几年。在新秩序建立十年左右之后,组织变化的步伐开始放慢,新的惯例也开始形成。
第五部分 合法性和政治能力第22节 合法性的含义
法律的根本力量在于它是一种国家的强制力量。只有国家才有实施肉体强制的特权(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是文明社会的一个特征。法律是一套根据国家对它的公民实施这一特权的要求而制定的规则。但如果法律不为公共情感所支持,它就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因此,法律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不是主要依靠警察力量,而是更依赖于公共意见和公共情感。
——罗素,《论权力》
强制只有施之于相对少数的人,并为许多人,最少是多数人支持和服从,而且有一个牢固的团体在行动上予以支持,它才是现实的。
——卡尔·多伊奇
在第四章中,我分析了组织年龄是制度化的核心要素的问题。但这只是说明了问题的一半。现在,我要对问题的另一关键因素加以分析,集中探讨国家政治组织的合法性问题。合法性是政治生命力的根本性、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它反映了那些寻求统治(也就是说,实施权力)的人为被统治者接受和认可的程度。它限定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的性质。
因为组织年龄本身对合法性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这二者是相互缠结在一起的。即使在韦伯的分析图式里,传统组织也因为人们认为它们一直在那存在着而从中获取权威。用更为宽泛的语言来说就是,传统制度被合法地认可和接受正是因为它们的年龄:服从于这些组织的人们也认可这些制度的权威,因为他们不能找到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可行的替代组织。随着岁月的增加,习惯也就形成了。
近期的研究也持相似的观点。例如,有一项对民间组织的更新倾向进行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新的组织要比其他的组织脆弱得多,因为它们缺少为其他组织认可的合法性(Singh,Tucker,and House,1986)。照这样,这种观点适用于作为法律实体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Jackson,Rosberg,1982a)。这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是更宽的国家体系中的一个法律实体,这一国家体系的大多数成员有着保持这一国际体系象原来一样存在并从中受益的持久的兴趣。因此,在国家主权得到国际承认——这表现在它们在不同的国际和跨国组织里拥有成员资格——这一意义上,大多数国家是享有合法性的。
当我们扩大我们的研究范围,把国家当成是一个拥有不同程度的国内政治能力的政治单位时,年龄对合法性的影响就会变得更不明确了。革命最具戏剧性地提醒我们旧秩序可能崩溃,但是即使在缺乏全方位的革命的情况下,公共机构的解体也并不常见。这种结局的可能性当然在对组织更新倾向研究的预料之内。这些研究毕竟没有说组织年龄能确保组织永远存在下去。相反,它们只是更适中也更准确地认为,组织崩溃的可能性随着组织年龄的增加而减少,但这种可能性永远不会为零(e.g.,Starbuck,1965,1983)。
既然组织年龄能减少但并不能消除组织的脆弱性,我们就需要扩大我们对国家政治能力的认识。这种认识的扩大包括对政治能力其他因素——合法性——的明确关注。在本章,我的意图是要说,对政治能力的研究不能离开政治合法性问题来进行。
在英文的政治学词汇里,很少有比合法性(Legitimacy)这一词因明确的原因引起了更大麻烦的词语。合法性通常被当成是可求的(desirable)。合法政权是那些能够成功地主张和维护自己真实可靠性、法律地位和有效性的政体,那些政权到处千方百计地促进、提高自身的合法性权力,这并不值得奇怪。相反,要想象这样一个政治宣言——一个比它的竞争对手成功地宣称“这一政体是不合法的,因为这一政体建立在有竞争对手能够提供一个它们自己的政治体制来取代现存的政治体制这一基础上”还更具毁灭性的政治宣言——是非常困难的。
正是合法性与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联系,降低了这个日常话语中的词汇的分析力量。在当今的世界,合法性这一概念常在合适的地方被用来区别界定政治体制的类型。随着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自决权的教义的广泛扩展,帝国主义统治无权象以前那样声称自己具有合理存在的特性。曾几何时,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被认为内在于官员取得权力的过程当中。在西方,政体常常是通过它们的“大众同意”(popular consent)的基础来判定的(正如选举所表现的),并通过民主原则来界定,这样,任何拒绝采用选举准则的政府本身就不具合法性。在西方世界之外的地方,衡量政治本质合法性的可行的手段多种多样(see,e.g.,Lane,1984;Nelson,1984;Rigby,1984;White,1986)。曾经一度有一段时间,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能且只能通过政策结果来判断。这样,不管政府取得权力的手段怎么样,那些更能带来经济增长或消除贫困和文盲的政府被认为是比其他的政府更具合法性(Epstein,1984;White,1986)。还有一些人认为合法性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 既然所有的政权都寻求对它们的存在的认可和承认,那么很明显,各种类型的价值观念都可被不同类型的政治秩序用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这充分说明了我们通常运用的合法性这一词语,它的分析效用是有限的。国家政治能力意指政府的程度,它独立于政府的类型。这种合法性观点与政府类型的比较有密切的联系(例如民主政府和威权政府之间的差别),在这一意义上,合法性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也就变得不很确定了。
与此同时,合法性这一术语的日常用法告诉我们,它的意义包括规范和价值。它是国家通过对诸如民族主义、平等和民主的意识形态象征的诉求所形成的产物。这些意识形态的诉求是用来在被统治者中间产生同意以便被统治者对政治秩序予以默认。这些努力诉求的形式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并依赖于它们发生的背景环境,但总体上看来,这些诉求本身就是政治生命力的核心。用吉尔茨的话来说,政府无时无地不对“你是谁,我必须服从你?”这一最为直接的政治问题作出回答(Geertz,1977,p251)。成功的政权是那些能够,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和手段,成功传播“政府是恰当地建立的,并因而有权进行统治”这样一种的总体的观念的政权。
象征产生合法性这一观点,意味着合法性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人们常把这一过程类比为舞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和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联系放在一起进行比较(e.g.,NettL,1967,chap.9)。 这种类比是有用的,因为它告诉我们,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自律机制可以简单地创造、处理并听任自己独立运作的东西。相反,合法性是一个需要掌权者自觉地、持续地加以关注和审视的东西。
这一类比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强调了合法性对于政治能力的中心地位。在第二章中,我对权力和暴力作出过区分,并认为权力的实施是具有相关性、依存性的,而且只有在那些服从权力的人把掌权者的要求和需要视为合理的也就是说视为合法的环境中,权力的实施才有可能。既然政治集中关注的是权力的运用而非暴力的运用,合法性也就称了民族国家政治能力或政治发展的根本所在。同意和服从在这里是决定性的因素。多伊奇曾清楚地论述过这一问题:
每个国家都必须发布命令。无论这些命令以什么形式出现——法律、政令、法庭裁决或是行政条例,大多数命令在多数时间里都必须为大多数人所遵守,如果国家想要延续下去的话。这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命令必须为人们所遵守,而且预期的结果也必须是这样。国家有效范围的制约因素也是制约大众服从可能性的制约因素,这二者都与命令有效贯彻的版图领土相关,也与可能服从的一帮人相关(Deutsch,1981,p341-342)。
如果一个政权不通过诉诸于暴力手段,就能够从大多数人那里引导出大规模的服从,那么,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个政权就是合法的。这种服从不必是全体的服从,但它一定要是广泛的、全面的。尽管人们对此持有相反的看法(例如Eckstein,1971,p50-56;Scott,1985,chap.8;Beetham,1991),在任何绝对的情况下,合法性不必一定要包含公民对政治秩序公正性的积极有效的信仰。不错,考虑到政治无处不涉及到价值性资源分配的冲突,这种结果很令人难以置信。相反,鉴于这种认识已为人知悉且又恰当可行,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合法性只是简单地要求一定程度的默认和对政治秩序总体上的合理性的认可和接受。
在对合法性的研究与葛兰西(Gramci,1971)对霸权(hegemony)的研究之间,明显存在着一种并行关系。与意指国家施加物质强制的统治(domination)不同,霸权有赖于通过劝服(persuasion)和操纵(manipulation)来产生同意。尽管前者对暴力的使用对于政治危机来讲可能非常普遍,然而霸权却是一套引导服从的“正规的”机制(Williams,1960,p591)。而且,霸权机制引导下的服从可能更为消极冷漠一些:
大众深深地把社会秩序当成是他们愿望的表现,因之而形成的同意(即被社会化了),远远不如因为大众缺乏那些——能使他们自己有效地理解并作用于他们的不同意(discontent)的——理性工具和“清晰的思想觉悟”所形成的同意(Femia,1975,p33)。
霸权通过压制能够想象得到的选择范围来产生默认,在这一意义上,它是成功的。
各种象征在合法化过程中被使用,但是在国家政治能力这一问题背景下,民族主义情感的表达或许最为普遍。合法化的目的就是要使国民形成这样一种广泛认识,那就是对民族国家制度的归属感要和他对其他的组织的感情纽带一样强大,甚至更为强大。用不同的话来说,合法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国民对民族国家及其制度的认同。
第五部分 合法性和政治能力第23节 种族地位与民族国家的合法性
我曾说过,现在的民族国家是一种相比而言较为晚近的国家形态。因为这些,连同这种形态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保护的事实,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倾向,它认为民族认同比其他认同尤其是比种族认同更为客观、合q理和现代(用韦伯的话来说,是理性)。然而,民族主义只是种族身份的其中的一种形态。二者都是一种边界不定的、一定认识和意识层次上的集团,任何一方都不比另一方更为具有任意性和传统性。因为民族边界的变化不定以及所有的民族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说都是多种族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常常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
即便在制度得到较好建立的国家,种族边界也经常模糊不清。在多语言的国家,例如在比利时和瑞士,这种情况非常明显。而在前苏联,各种族团体的“俄罗斯化(Russisfication)”却是一个持续性的政治问题,并最终成了爆炸性的问题(Silver,1974)。尽管在其他国家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这一问题依然存在。例如意大利的统一相对而言是较近的事,但意大利正象现在所表现的那样,并没有把所有讲意大利语的欧洲人统合进来。在加拿大和西班牙,民族统一前景仍不明朗。象英国那种呼吁建立同质单一民族的持续性种族政治运动,它加剧了民族认同的脆弱性和松散性。确实,这些民族运动构成了对国家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直接的威胁。
在新兴国家,这一问题更为明显。尽管1947年在印度次大陆,沿着宗教边界进行了分治,但接下来种族问题成了巴基斯坦分裂和印度联邦主义的基础,种族冲突成了该地区的持续性的现象。旁遮普和斯里兰卡的事情只是这种种族摩擦的一种更为明显的表现而已。即使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中脱离出来了,但对种族的考虑一直在马来西亚政治中有着突出的地位。尽管伊拉克的种族问题是一个特例,但是种族一直是伊拉克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这表现为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的争斗。或许当今政治中的最引人注目的事例可以在次撒哈拉非洲找到,在那里,国家边界混乱不堪,它们是上一世纪欧洲殖民国家为谋求那一地区的利益而在军事和经济上激烈竞争的结果,这种边界状况与种族边界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就这一模式,请参Rabushka和Shepsle,1972;Young,1976,尤其是第三章;Young,1988,p37-48;Jackson 和Rosberg,1984a;Hobsbawm,1990,p171)。
在许多政治发展的研究文献里,这些问题被称为“民族整合(national intergration)”的问题。总体上来说,种族是国家政治能力问题的中心,尤其是合法性问题的核心,因为正如我在上文指出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种族意识的其中一种形态。种族一词源于希腊语“ethnos”一词,意指有共同血统的一群人。正如霍罗威茨(Horowitz,1985,p53)指出的,种族单位的内涵多少有些弹性,但它最少是指它的成员相信自己与众不同并首先通过家庭关系来繁衍的这样一种社会单位。“这样,种族就容易把由不同肤色、语言、宗教分化出来的团体包括进去;种族包括宗族(tribes)、族群(nationalities)、种姓(castes)、人种(races)各种形态”。但无论它们是哪一种形式,种族集团有着一个共同的重要要素:它们都建立在反映生命特性并为个体提供种族认同的原始的情感基础(Geertz,1963)上。
但是民族主义不只是一种种族的体现形态。很早以前,民族主义就象今天一样获得了它们的政治意义。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他的《代议政府论》(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一书中提出过这个问题。
如果他们通过在他们与其他的人群之间并不存在的共同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统一在一起,那么人类中的那一部分人可以说构成了一个民族…这种民族感情可以因许多原因产生。有时候,它是族群和血统认同的结果,而语言共同体、宗教共同体更是它的直接成因。但是这里头最重要的是政治祖先的认同(斜体为原文所加),是拥有共同的政治历史,因而重新聚合形成的共同体,共同的荣辱兴衰,悲喜遗憾,这些都与过去的同一事件联系在一起(John Stuart Mill,p 861,chap.16;)
大约在六十年前,萨拜因用相似的语言来定义民族:
民族是指一个文化统一体:对共同领土的忠诚感情;共同的语言和文学;认同于共同的历史和英雄;共同的宗教。最根本的或许是政治自决的强烈愿望(Sabine,1934,p329)。
爱默森在结论中重复了上述这一观点:
对民族能作的最简单的定义是:民族是一个由认为他们是一个民族的人们构成的实体;而且当所有精心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时,这可能也是最终的说法…有许多人在对民族进行定义时…认为民族由领土、语言、共同的历史传统和国家与民族之间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四个因素构成,这四个因素将持续再现,而且是形成共同的命运认识的根本(Emerson,1960,p102-4)。
这里最有意思的东西是,认为价值和规范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就象它们也是种族性(ethnicity)的核心一样。而且,象种族性一样,民族主义也求助于共同的历史和政治传统。种族团体和民族主义团体的唯一的一点差别是前者并不要求政治自决权。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e)明确地总结出了它们的差别:
国家是这样一个政治实体,其中有一部分人声称对另一部分既非亲族也非配偶的人拥有权威,而且举国都为这一部分人所占有。种族集团是这样一个团体,其中,人们声称有共同的血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民族是政治上觉悟了的种族,在共同的种族性基础上,声称享有国家地位的权力。(Van den Berghe,1983,p222;还可参Gellner,1983)。
这种差别因而说明民族情感和种族情感一样都是原始和传统的。由于同样的原因,种族地位也和民族主义一样现代。
在民族国家背景中,合法化进程包括合法性的创造和在普通居民中对它进行灌输。在这些居民中,新的基本认同取代、至少是压倒旧的基本认同,这样国家就成了居民认同的“终极的共同体(terminal community)”(Emerson,1960,p96)。这个国家统一的进程在早期对国家整合问题的研究里占有核心地位,它把国家整合当成是一种“领土范围内的国家感”的创造,这种国家感使次要的地域性忠诚相形见绌甚至消失(Weiner,1965)。换句话说,这一国家整合进程是要努力创造出一个神话,这个神话象征着一个可资认同的集体、一个新的传统,或者象征一个——用安德森(Anderson,1991)的更贴切的话来说——想象出来的共同体。 这里的矛盾至少在三个特别的而又重叠的方面被明显加深了。
首先,要低估种族纽带的原始特性的意义很困难。既然种族集团的边界是可以变动的而且对它的理解也变化不定,那么种族地位本身也就与人们对种族存在的基本认知,也就是与个人认同密不可分了(请参Smith,1987)。这样,对各种团体的认同进行整合的努力也就定会遇到可怕的障碍。种族与“国家”之间的这种张力,尽管并不是在新兴国家才会出现,在单独使用暴力那种情况下也会发生。吉尔茨在三十年前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
在新兴国家,这种紧张关系表现得特别严重,持续的时间也特别长。这都是因为新兴国家的人们的自我认知与血缘、种族、语言、地域或传统的大概的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关系依然紧密,也因为在本世纪作为实现集体目标积极有效的工具的主权国家的重要性的快速稳定的增长。多种族,通常就意味着多语言,有时候也意味着多人种 ,新兴国家的人们倾向于把那些直接的、具体实在的、对他们而言差异模糊但又意义深远的归类当成是他们个体特性的基本内容。把特殊的、常见的身份认同置于次要地位,这有助于形成一个包罗万象并多少有点陌生的公民秩序,但这要冒失去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人这一意义的风险,他们要么通过被一个文化上没有分化的大众群体所同化,要么被其它一些能以自己的个性深深影响社会秩序的敌对的种族、族群或语言的共同体所控制和统治,并使他们失去自主性和独立性(Geertz,1963,p108-109)。
第二,正如我在第一章中已经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起云涌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把民族主义和贴上代议制标签的民主意识形态连接在一起。这种意识形态为非殖民化运动提供了一种政治合法性,这表现在“民族自决权”这一原则上。这一原则是非殖民化运动的基础,并为动员大量的国民反对相应的殖民权力和支持那些致力于本土民族主义的政治权威集中化目标的民族运动奠定基础。这从而有助于形成一种“我们对他们(us—versus--them)”的情感,这种情感能为任何原始组织打下基础(Armstrong,1982)。果真如此的话,这一情感就培育出了一种与这些集团相联系的民族历史的认知感。
尽管这种民族情感的动员是推翻殖民主义的关键,但也为第三世界的政府在后独立时期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尽管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必定已经发现这种相反的结果,但对这一点,有学者早就有所预料。正如阿普特所说的,
在新兴国家里,掌权的政治领袖忙于对殖民权威进行挑战,并削弱人们对殖民政治统治的服从。在一定程度上,当大众激情和革命热情开始衰减,那些政治领袖也就为他们自己创造的体制和权威埋下了不稳定的祸根(Apter,1963,p81)。
阿普特的研究提醒我们,一旦大量的人们在民族自决权的旗帜、口号下被动员起来,要解散他们却非常困难。相反,这一同样的旗帜和口号可能被国内抵制和反抗新秩序的集团用做证明“造反有理”的工具。民族主义运动几乎只是一个松散的种族和阶级联盟(请参Clapham,1985,chap.2),因此它天性脆弱。在种族集团彼此分裂时(因为它们大多数是多语言的国家),问题尤为严重,因为这些集团能够更有说服力地威胁要退出联盟。在这种情况下,种族分裂带来了“巴尔干化的幽灵”,这一幽灵在大多数内战中显现出来(请看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的例子),并在前南斯拉夫的事件中得到复活。
这种种族分裂并不会产生问题,它只不过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加剧。即便这一问题在新兴国家最为明显,但这也不是一个只在新兴国家才会出现的问题。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从菲律宾的“新人民军(Huks)”到西方国家常常提到的种族生存,到前苏联帝国,它到处为种族情感提供正当、充足的理由。
第三,对种族政治来讲,社会流动和政治动员一样重要。和多伊奇(Deutsch,1961)一样,我用社会流动这一词来界定伴随着工业化和新技术的引入而产生的变化。这里的变化尤其是指大众交流(mass communication)和大众媒介的变化。社会流动是重要的,因为它增加了组织之间的联系和接触,并使它们更能意识到彼此的存在。这样,反过来也就增加了这种可能性:国家内的各种族集团之间认为各种族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的地位。正如多伊奇早先指出的,
在那些国内居民因不同的语言、文化或者基本的生活方式而分为几大集团的国家里,迅速的社会的流动可能会限制甚至毁灭国家的统一…由于各单位居民或统治者个人在以上任何一方面根本不同,社会流动可能会抑制、阻止国家或政治单位的融合,至少是使这种融合更为困难(1961,p501)。
社会流动确实可能有助于建立一种种族自觉意识和它觉意识(请参Melson and Wolpe,1970;Milne,1981,第五章;Nielsen,1985)。在多伊奇写作此书的那些年后,随着电子媒体——它能提供一种能力,使得政治信息的流动迅速而又生动(图文并茂),而并不要求信息接收者一定是一个有很高文化的人——的传播和普及,社会动员的速度成几何级数增长。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可以预见,种族政治的地位和作用将得到增加。
我并不是说种族性是民族国家冲突的唯一基础。本世纪发生的一些主要的革命运动都是清楚地受其他因素所驱动。民族主义只不过是种族性的一种形态,仅仅在寻求象最高共同体(指主权国家)那样的终极最高认可的意义上,它才显得比较特别,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近期的政治史中,种族冲突那么突出。这一事实还告诉我们,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关键所在的国家认同,只不过是种族认同的一种特殊的情况。在涉及归属问题的原始情感这一基础上,创造传统和合法化传统(即价值观念的灌输)的矛盾明显会使这一进程坎坷曲折、充满风险。
在另一层次上,这又促使我们回到组织的更新倾向的问题上来,因为传统需要时间来演化、变迁。而且,确实,老的国家在国家政治传统上占有优势,即便它们的制度合法性远远无法得到保证,它们还是可以充分利用自己悠久的政治传统。这些传统在人们心中已成了一座用语言和军事历史等因素来象征的无形的“政治纪念碑”(de Schweinitz,1970,p535),从而提供一个根本区别于次国家的种族认同的、清晰可见的、持续的国家认同。
由于同样的原因,认为老国家政治上更为先进,也是一种误导。在它们总体上更为富有这一意义上,它们当然比别的国家享有着技术上的优势。但是它们用来加强自身政治合法性的国家传统并不一定天生就更为现代和先进。相反,它们只是为共同体的国家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只是建立在种族因素基础上的认同体系的一部分——提供一个基础(Smith,1987,1988)。
而对于新兴国家来讲,必须形成一种“有共同的过去的认识”。在很多情况下,非殖民化运动通过创造本土的政治领袖和政治组织——这在独立后又成为民族主义的、一党制的基础,本身就为自己提供了部分必备的共同历史。或许更重要的是,非殖民化运动对确定共同的外部威胁很有帮助。外部威胁,当然强化了“我们对他们(us-versus-them)”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是种族集团和初生国家——它们正是通过排他性原则和区别原则才与其他集团划清界线——的特征(Armstrong,1982,chap.1)。这些东西是帮助建立“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的基础和关键,这一“政治宗教”通过把政治秩序象征为一个全体性的实体,通过区别“善良的”和“丑恶的”,通过认定现任领袖是好领袖并把他们和作为总体的政治秩序联系在一起,总之,这一政治宗教通过以上种种手段使得国家合法化。
独立后,通过确定一个带来外部威胁的共同的敌人,来为民族国家的合法化提供一个持续的基础。这种经历在象以色列那样的国家非常明显。在以色列,军事和明确的外部挑战一起帮助整合了一个文化多种多样的国民。在卡斯特罗的古巴和桑地诺的尼加拉瓜也有着相似的经历,在那里,来自美国的军事压力被用作国内特定政治体制合法化的工具。更为普遍的是,新殖民主义的幽灵也再三地用来使民族政治领袖的意图合法化。确实有人认为,许多老牌第三世界国家比它们可能拥有更少的合法性,因为它们最近缺乏一种殖民的痛苦经历,而且缺少外部主要的军事威胁。因此,斯科特(Scott)就得出结论说,“外部入侵的威胁和对殖民地经历的痛苦记忆是促使各种根本不同的利益团体在政治进程中得以合作和整合的最强大的因素……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那么正是这种动力因素的缺乏,使得拉丁美洲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分离开来了”(Scott,1963,p83)。
第五部分 合法性和政治能力第24节 政治合法性研究的意义
当然,并非所有的对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挑战都建立在种族基础上。但是,种族挑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大多数仍然保留有多种族) 的一个持续性的特定问题。把民族主义视为种族性的一种形态,正是为了强调和突出政治合法性的关键的组成部分。
首先,合法性不是一个极端性的东西。这是因为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对其国民使用暴力,并且这种能力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即便情况不是如此,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秩序能够声称具有完全的合法性。相反,所有的政权都力求在相关的政治集团中形成一种对程序的有效共识。但是民族边界象种族边界一样是变动不居的。既然民族自决权这一现代原则意义非常深远,相关政治集团的规模会随时间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那么那些集团的基本利益也就常常会发生冲突。因此,合法性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
在任何绝对的意义上,把政体看作不具合法性都没有多大用处。相反,用连续性的标准来看待合法性倒更为有用,当合法性的损失超过了临界点而且存在着一个与它分庭抗礼并可以用来取代它的政治秩序时,旧的政治秩序就会被推翻或取代。让我们看看二十世纪俄国、中国和伊朗的革命,看看菲律宾马科斯政权的倒台,海地杜瓦利埃政府的崩溃,看看希腊和阿根廷军人政府的终结,或者看看次撒哈拉非洲国家此起彼伏的军事政变,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门槛、或临界点的位置在各种情况下都会不同。因此合法性总是处于一种波动的状态。
其次,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之间的关联告诉我们,合法性总是与价值有关。特别的是,国家政治秩序被视为可靠可信的程度取决于它们被国民接受的程度,取决于相关人口认同它们的程度。既然政权能够采用各种策略来使自己合法化,这些价值的形式和内容在各种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样,一个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就不能根据这个政治秩序的形态——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或民族主义的——来作出判断。
相反,无论一个政体的意识形态的取向如何,我们都必须根据这一政权的政治行为来评估它的合法性。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政体是否形成了一种服从,或是否建立了一个政治活动得以进行的框架?既然政治指的是权力或权威的实施,那么随着和平、平静地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加强,合法性也就得到加强。这样,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就应根据解决它们冲突的能力来判断,这种冲突的解决应该是对实际的或潜在的对手不使用暴力手段,同时不动员别人来反对或抵制自己的竞争对手。我将依次对这两点进行讨论。
第五部分 合法性和政治能力第25节 物质暴力的官方使用
我已经强调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所有国家的政治秩序都有能力使用强制手段。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但是我也强调过对暴力手段的连续的依赖根本上就是非政治的,而且它也代表了一种权力的丧失。这是权威对暴力的持续使用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的结果。在它们的官方地位已经产生问题的意义上,这种行为意味着那些“权威”不再被视为是真正的权威。
既然就一部分国民而言,权力和权威的实施要求一定程度的服从,在国内舞台上,政权对暴力的依赖不言而喻是合法性丧失的表现。因为合法性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这种丧失不一定是彻底的、完全的丧失,尽管如此,但它依然是一种丧失。倒退到物质暴力的使用反映了不能以代价较低的方式来引导服从这一事实(请参Mason,Krane,1989)。官方暴力的持续使用将付出代价这点,在政权到处试图掩盖、隐瞒这种行为上得到了证明和体现。
在最后一部分,我已经提到,政权在促成人们认识到它们是恰当地组建起来的这点的具体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与其他的东西比较,这种不同反映了政权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取向。要形成对同意产生的程序进行评估的公共标准很不可能,因为没有单一的程序。但是,我们没有对同意如何产生这一问题有所偏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把它看成是政治绩效的问题,那么更为基本的问题就是,这种同意和服从是否根本有效地形成了。我对政权使用暴力的强调正是为了研究这一问题。
国家的物质强制或镇压可以采用很多形式。根据它们的严厉程度来分,程度最轻的形式包括为了约束挑战者,对总体的政权或政治秩序所作的政治动员,对个人或团体政治活动采取的物质制约。对政治集会的禁止和取缔,对政治活动家的逮捕和监禁,对政党的取缔等等都是这种限制的典型形式。尽管国家的这些惩罚相对较为温和,但它们依然是物质暴力的使用。对这些手段的使用表明,他们已经承认不能通过谈判或通过其他的优越于谈判的政治手段来促生服从。
官方强制的严厉性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增加。第一,政权可以继续使用相同的策略,但是,不是孤立的、个别的、零散的使用这种策略,而是更为系统、更为持久地使用这种策略。对政党的取缔和禁止也从短期的取缔变为永久的取缔。与此相似,对反对者个人的短期的拘留也转变为长期的监禁,并常常包括军事管制和戒严的实施在内。这些措施是要通过持久的恐吓和威胁来增加对国家的不服从和反对行为的成本与代价。
第二,政权可以通过加强对挑战者的身体伤害程度来逐步提高暴力的层次。反对者现在遭受的不是监禁,而是毫无声息的永久消失。死刑政治犯的数量增加了。现在不是简单的禁止政治集会和逮捕那些藐视禁令的人,而是开始对反对者动用致命的暴力。致命性暴力的使用可能是偶尔为之的,但它常常会演变为政权的一种持续的行为模式。即便它是间断地被使用的,然而暴力的这种运用明显地是要增加挑战政治秩序的代价和成本的。
对使用暴力进行的大多数研究都把这种现象描绘成“镇压”或“国家恐怖”(请参Gurr,1986a,1986b)。这种观点常常和西方自由标准下的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要对这种观点和相关的书籍有所了解,请参Donnelly,1984;Howard和Donnelly,1986)。我是在不同的用法上来使用“运用暴力”这一词语。与把暴力使用看成是人权问题的观点不同,我把国家使用暴力看成是国家政治能力或国家权力的一个要素。既然所有的国家都拥有强制的工具,那么它们越不使用暴力,就越能说明它们的政治能力越强。对这种差异的强调说明了我的见解,那就是除了镇压产生被迫服从这个明显的问题之外,国家对物质强制的再三使用也已经演变成为掌权者实施权力的主要障碍。
有些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请看布迪厄(Bourdieu)的看法:
对暴力的温和的、隐含的使用是使用暴力所采取的形式……无论在何时公开使用暴力,但残忍粗暴的使用暴力总不可能……暴力的温和使用是由经济资本向象征资本的重新转变,这种转变是无尽头的,也是代价高昂的(Bourdieu,1977,p192-195)。
在利用这一观点和其他的人的观点基础上,斯科特(Scott)得出结论说,“在直接的物质强制不可能的情况下,在纯粹间接的支配资本主义市场还不具备足以独自保障他们的剥削利益的效能的地方,就必定要使经济权力含蓄化”(Scott,1985,p307)。这样,物质暴力的使用(公开的、粗暴的使用)就被看成是一种比政治权力的实施(温和的、隐晦的使用)更为有效的控制模式。
这种解释模式的问题在于,它们对与两种方法相关的成本计算是不完全的(而且它们都忽略了这两种方法可能产生的好处)。特别的是,因为权力的实施需要作出持续的努力去合法化,而且“经济资本向象征资本的转变没有尽期”,因此,人们认为权力的温和实施付出的成本也会更高。是的,这里确实含有成本因素,但是它也能带来服从甚至对政府予以积极支持等等的好处。同时,这种观点完全忽略了物质暴力的使用也必须承担——从中断生产的角度来看——更高的经济成本和其他成本。而且粗暴的使用暴力的好处可能是非常少的。比如说,暴力不能产生服从,也不可能产生积极有效的支持。
尽管建立在多少有些不同的计算的基础上,蒂利(Tilly)等人认为,国家及其挑战者作为权力斗争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它们都采用暴力,这一著名观点与此非常相似。他们把这种斗争看成是政治过程的基本要素,并得出结论说“镇压开始了”。更为特别的是,
政府的任务是要使它们与对手相比的地位最大化,并在它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维持这一压倒性的权力优势的结构。政府公职人员因此应有一套有别于挑战者的成本收益的计算方法。他们有机会使用集中的镇压力量。尽管有着与此相对的自由神话,暴力镇压机器开始发挥作用运行了。它的作用的发挥是短暂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作用的发挥甚至更好:就我们所知的,认为长期为暴政所困扰的一个国家的居民,最终会因失望而奋起,并为砸碎枷锁而做出任何事情,其实这种观点是不真实的。实际上,那些被压制的居民没有动员起来,他们只是以当局认可的途径来从事集体行动,并寻求以非集体性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目标。在对集体行动给予的惩罚——对行动者进行伤害或拘捕——将降低集体行动的频率和强度的意义上,镇压机器才会发挥作用。这样,一般来说,政府暴力途径的选择比政府挑战者的暴力选择效果要好得多(Tilly,Tilly,andTilly,1975,p285)。
但是蒂利的这种观点模糊了几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同样是蒂利他们,继续声称,挑战者对政府的集体性的抗议行动在很多情况下同样能发挥作用。他们主张说,当挑战者的目标有限和具体时,他们就很可能会取得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并不普遍,即使挑战者的目标更为宽泛些。此外,蒂利他们相信这是一种普遍的模式,并不是只在最近一百五十年的欧洲历史中才能发现的唯一现象。然而,以这种形式来表述这一观点,说明他们试图采取骑强态度,在这一情况下,主张暴力发挥作用这一观点的意义就变得不明确了。是的,镇压给挑战者带来了代价,但这是否能说明这种手段总的来说就会行之有效?蒂利等人还认为在压制和集体性的暴力之间存在着一种非直线的关系,其中后者最为明显地是一种高层次的压制,但不是极端形式。这种观点与早期的研究相吻合(例如Gurr,1968),但是,这并不表明压制的有效性,尤其从长远看来更为如此。
蒂利他们的结论存在的第二个一般性的问题是,他们把政府描绘成一个统一的行动者: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被看成是一个防止底层挑战者的挑战行为的行动者。但是对政府的最常见的挑战并不是来自底层。相反,把政府看成是一个包括军队的利益联盟倒更为可行,而且所有的联盟都是脆弱的。国家公职人员采取的暴力行动很少只直接指向底层的挑战者,还包括对联盟内部的一些人采取的暴力行动。有鉴于此,暴力的使用可以分割为为公民利益和为军队利益采用的暴力行动,而且即使在军队利益内部也可以强化其中的派系。政府联盟的脆弱性直接增加了这种分裂的透明度、清晰度。正如大多数军事政变所明确表现出来的一样,对政府联盟内部的暴力威胁和暴力使用毁灭了这个联盟,并因而导致内在的动荡不定。一旦我们承认政府(或国家)不是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行动者,那么从长远看来,要说镇压可以根本上认为是行之有效、值得一试的策略,其原因就极不明确了,也是令人费解的。
第三,就象杰克逊和罗斯伯格(Jackson,Rosberg,1982b)以及胡奇罗夫特(Hutchcroft,1991)所使用的一样,压制性政府这一词语常常是指个人政府。典型的事例包括杜瓦利埃独裁下的海地政府,弗朗哥独裁下的西班牙政府,阿明的乌干达政府,以及马科斯的菲律宾政府。由于它们是个人独裁的政府,因此它们可能极不稳定,其中原因我在第三章中已经作出过解释。当然,这种不稳定的结果可能只是因为一个残暴的政府为另一个具有同样残暴癖性的人所继承。正如国家的许多前任首领和他们同伙已经所发现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压制只为第一届政府发挥作用。
当然,蒂利等人提出的观点确实包含着真理的因子。确实所有的政府最少都具备一定的镇压能力,而且镇压理所当然地增加了政治挑战者的代价。此外,类似斯大林在苏联的清洗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严厉的镇压可以使潜在的挑战者长期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但是这种观点和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压制要么有利于产生合法性要么有利于产生政治能力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与采纳这一立场相反,去理解镇压策略对那些依赖于这一镇压手段的政权会带来什么样的代价却更为有用。甚至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政权还在缩小了的层次上使用压制这一策略,而且有充分的事实表明,这种压制日益成为促使自己的国际支持最大化的不同程度的积极(象征性的和物质的)的诱因(请参Lane,1984;Rigby,1984;White,1986;Silver,1987;BahryandSilver,1987)。
当压制的代价得到承认,这一压制策略对合法性的害处也就显而易见。我承认,为追求政治目标(尽管有些政府使用这一策略比其他的政府更为频繁),很少有政府会完全放弃物质强制策略的使用。但是这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明这一观点:合法性总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且永远不能被理解为一个极端性的东西。
第五部分 合法性和政治能力第26节 对政治秩序的挑战
合法性的反面包括积累起来的对政治秩序的挑战。既然,正如我早已强调过的,政治集中关注价值性资源的分配冲突,那么所有的政权都同时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对。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种反对的性质是什么。既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考察这些挑战,我们的意图就是要对那些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来表达和传递的挑战和不能通过正常途径来表达和传递的挑战作出基本区分。超越“正常渠道是政治能力问题的关键”这一主张,正常渠道就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尤其是,如果那些正常渠道确实能够容纳大多数政治需求,那么它们就可以被看作是合理的、有效的,并能使制度合法化。自然,对后一句话而言,有着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只有在政权没有同时对政治挑战者施加强大的镇压时,这个论点才能适用。如果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或者最少基本满足,那么使用那些正常渠道来表达和传递政治需求,就意味着那些渠道总体而言是可靠的、真实的、合理的。
另一种形式的挑战发生在正规的政治制度之外。确实,如果我们记住这种称号指的是挑战的实质而非挑战的频率,那么这种形式的挑战就可以被理解为政治参与的“非正规、不合法的”形式。我在使用这一术语时,它指的是一套多种多样的、异质的行为。根据那些事件所涉及的严重或温和的程度,它们是指从对政府特定政策的非暴力抗议(包括静坐和游行等等)到推翻旧秩序并用新秩序取而代之的全方位的革命范围内的行为。通常的情况是,相对温和的抗议活动会演变成包括暴乱甚至内战在内的暴力形式。而且,这些行为包括了但不局限于那些具有大众基础的行为。例如,军事政变就是这样一种挑战,即便它们由一小部分人实施并高度保密。最后,这种挑战未必都是非法的,但是是不正规的、不合习惯的,因为它们不是通过正常渠道来达到目的,并且对于挑战者来说,他们最少还威胁使用暴力。
这种通过非正常渠道的参与形式,它的特征就是对挑战者而言可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请参Eckstein,1980,p158-159)。根据两种行为采取的形式和可能产生的结果,与正常渠道的挑战相比,非正常渠道的挑战更少组织性、条理性,因而也更少可预见性。而且,这种行为更可能要冒来自权威作出反应——通常是指对挑战者进行镇压——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增加了非正规形式的对抗性参与的代价和成本,而且这种成本随着这种挑战暴力程度或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假定那些挑战者不愿承受那种代价和风险,那么他们选择通过非正常渠道来进行挑战就说明了这样两个相关事实。第一,它表明,他们不相信正常渠道能够为他们追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机制,并直接声称那些渠道形同虚设,不具效用。第二,它意味着他们估计到,他们有机会来获得更高的利益,并用它来抵消增加了的非正规参与行为的成本。这种估计有许多原因。例如,这种估计可能源于他们对现状、局势的判断,他们可能认为局势是如此之坏以致任何行动都是可取的,或者可能源于他们的这样一种推算,正常渠道的无效性充分说明了政权对它的挑战无能为力、政权不堪一击。尽管这种推算会从一种情况到另一种情况变得不可靠,尽管推算本身可能是相当的不确定,重要意义在于,这种估计的存在直接证明了对政治秩序合法性提出挑战的重要的集团存在着。
政治挑战的非正规形式的思想直接源于第二章中我对权力的分析。正如权威对物质暴力手段的持续使用会削弱权威的政治基础一样,参与的非正规形式也表明了政治能力的衰退和下降。这种视角与对抗议的探讨——它们把这种现象视为是相对无权的集团试图通过谋取第三党的支持,或通过增加政府因忽视它们的利益和偏好所付出的代价,来为自己创造政治资源——并行不悖(请参Lipsky,1968;Wilson,1973,chap.14)。根据这一观点,求助于抗议本身就说明它们的政治地位的相对弱小:根据定义,更有实力的挑战者占有着充分的资源,它们可以避免采用这种策略,并通过正常的制度渠道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贯穿于所有这些内容(包括我在本章最后一部分对压制的探讨)的主题是:政治参与者在政治舞台上理性地行动,为的是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为自己获取尽可能多的好处。所有的政治参与者,无论他们是权威者,权威挑战者,还是相对并不活跃的公民,他们都能各得其所,把自己置于最适当的位置。他们的计算并不局限于经济上的考虑,相反,他们把政治和社会因素(就象经济商品那样计算)也计算在内(请参Wilson,1973,chap.2)。与此同时,他们的有利行为又受到所有参与者信息不完全的限制。这导致他们的成本收益计算变得不确定、不精确,这又反过来意味着,他们的政治决定常常产生预料之外的结果。
工具理性的“信息不完全”的假设,这被广泛地应用于对投票和政党行为等正常形式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分析研究(请参Downs,1957;Fiorina,1990;Aldrich,1993)。这种分析当然与游戏规则相对明确的背景和环境有关。但即便在那种背景中,政治行为仍然受到与计算不确定相关的代价的制约。当我们回过头去对包括非正规形式的参与在内的挑战进行研究时,这个问题也就扩大了,因为在这种环境中,游戏规则更不明确,局势也更扑朔迷离、变化不定。规则越模糊,参与者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大。随着政治行为可预见性的下降,成本收益的计算也就风险更大,而且即便所有的参与者都理性行事,产生预料之外和不合心意的恶果的可能性也会加大。
这就是为什么不合常规、不依惯例的政治行为所付出的成本要比制度化、惯例化的政治参与行为付出的成本要高得多的原因,这说明不按规则行事的人期望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和好处。即便其他方面都和不按惯例一样,来自惯例和制度的可预见性也是更佳的选择。在这一意义上,依赖于非正规的行动就等于承认所有其他的方面都不相同这一事实。这进一步说明政治制度在容纳各种政治要求、政治怨愤和政治挑战上是失败的、无效的。非正规行为的存在至少从表面上表明制度已经失去了合法性。
尽管这种观点有很多地方表现得明了、简洁,但它与国家政治发展研究里的对政治参与的解释有着明显的不同和偏离。对参与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对政治参与的价值总的持矛盾的态度。 即便是在对民主制度得到很好建立的国家的政治参与进行的研究里,也有许多人认为,参与只是不能同时得到重视的诸多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价值之一。这样,人们常常听到较高的大众政治参与率未必值得追求,因为较高的大众政治参与常常削弱政府有效行动的能力。因为对是什么刺激了政治行动,大家意见不一,这样矛盾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尤其是,人们常常认为,对许多人来说,在考虑政治行为时,包括社会失范感(比如颓废、迷惘、焦虑)和个人的异化感、疏离感在内的相关的情感因素和功利因素同样重要。即便正常形式的大众参与也可能为非理性的感情因素所支配,这一看法使得许多学者对正常渠道的政治参与的高比率是否值得追求,也深表怀疑(要对这些观点有进一步的了解,请参Jackman,1987)。
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参与的非正规形式上——人们常常把它们视为是一种社会病变而不是一种政治行为,并把它看成是没有任何根据和来由的结果,而不是把它看成是成本收益计算的产物——时,矛盾更为明显。这样,康豪塞(Kornhauser,1959)在他1959年的经典性的著作中认为,这种行为只是由个人脱离社会造成的极端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是大众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原子化(atomization)的产物。这样,就其本身而论,它只是一种为宣泄侵略意向而作出的一种简单的情感反应,它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政治内容。
奥尔森在他的那篇关于快速经济增长产生不稳定效应的深具影响的论文中,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增长是一种使社会产生紊乱和错位的力量。它削弱了旧有处理问题方式的力量,以致有很多人认为自己的情况比以前要更加糟糕。那些新近不稳定的人正是那些可能进行非正规的政治活动的人:“他们往往因相对缺少与社会秩序相互连接的纽带而显得有些特殊。他们往往对构成社会的任何社会次团体都没有密切的感情和忠诚”(Olson,1963,p532)。这些新近落泊流离、失去地位的人,他们的参与并不是围绕一个明确的政治议程而展开,相反,他们的参与行动只是一种情感的、非理性的迸发,是对社会变迁几乎同时作出的反应。
亨廷顿关于政治衰朽根源的观点,是对这种观点的扩展和延伸,他对政治参与有着相似的看法,认为它只是一个随“社会挫折”而发生变化的因变量(Huntington,1968,p55)。在普利夺(praetorian)社会中,缺少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融合社会矛盾和纷争,各种社会势力相互直裸裸地对抗,大众政治只是摆摆架势、摆摆样子(1968,p196)。对那些社会力量代表个人和团体去为他们谋求政治利益的可能性,学者们给予的关注不够。相反,他们把重点放在参与带来的社会混乱上,而且这些社会混乱说明了政治的无序,精英们也无法去防止它们。
约翰逊(Johnson)在他对革命的著名的分析中,也明显有着与此相同的见解。他认为,迅速的社会变迁削弱了社会均衡。社会制度失去平衡是革命的前提条件,它还使所有的人产生个人紧张感。意识形态是这一切的推动因素:“意识形态从何而来?它们是由那些受个人心理需要、生活经历、社会失衡导致的紧张或所有这一切的联合所驱动的人创造出来的”(Johnson,1982b,p88)。这种观点的关键之处在于:那些从事非正规政治活动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已经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他们不知所措。社会控制的无力和缺失造成了人们需求和焦虑的表达的失范。
此后不久,爱克斯坦(Eckstein)声称,许多政治行为,尤其是叛乱和反抗行为,是没有目标指向的。相反,因为它们反对利益、效用的最大化,他们承担的痛苦也就最小化。但是,按照爱克斯坦的看法,因为痛苦最小化的努力建立在挫折的基础上,痛苦最小化并不可能是他们的行动目标。这样,非正规形式的参与就缺乏政治目标和政治决心。
人们一般把非正规形式的参与当作是使得社会结构支离破碎的病态行为。我很难说得上是认为这种一般看法源于迪尔凯姆(Durkheim)的第一人(请参Tilly,1978,chap2;Kohli,1986;Rule,1988)。这些行为更多的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根深蒂固的心理欲求的一种表达,而不是把它当作是一种政治挑战。迪尔凯姆早就在《自杀论》(Suicide)中就粗略地论述了这种观点:
随着社会的不断繁荣,人们的要求和欲望也相应增加了。正在那时,传统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权威,人们越来越大的胃口使得他们的要求变得更加迫切,而且他们对控制也越来越感到不耐烦。社会的失范状态因而进一步被缺乏规制的激情所加剧,而这时正需要更多的规制(Durkheim,1951,p253)。
但是,把非正规的政治参与形式当作是对社会变迁作出的难以控制的意
识的、本能的反应,这扭曲了原来的问题。它使得我们所预料的行为要比实际发生的要多些。毕竟,近年来技术的扩散成指数式增长,这种增长引起了迪尔凯姆提到的那种错位的变化。但是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表明,这种技术扩散的指数式增长导致了失范行为(或者说对政治秩序的挑战)也呈指数式增长。社会行为失范论的解释没有说服力,因为它忽视了使用这一策略的人要付出的潜在的成本和代价。如果我们以一种忽略那些成本的方式来看待问题,那么对在什么情况下挑战者才会感到自己应该在正常渠道外行动,我们就更不可能理解。当然,这只是一种经验上的失败。
尽管如此,但把非正规形式的参与看成是一种畸形的心理反应,就是贬低这些非正规形式参与行为的政治意义。这种看法把这种参与行为当成是需要加以控制的突然迸发,但它缺乏一些有意义的成分,那就是:把它们看成是一种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的挑战的观点被排除在外。此外,因为它们是对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反应的突然爆发,因此这种参与行为与政府的行为根本无关。
考虑到存在这些问题,我们不如把非正规形式的参与行为当成是受理性驱动的。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行为是有用处的,承认不确定性并因而包括成本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也是有意义的,而且这种观点强化了这种参与行为的政治基础(Jackman,1993)。 毫不奇怪,这些事实表明这样一种理念和思想更有助于我们去对挑战发动的机制(Tilly,1978;FiremanandGamson,1979;DeNardo,1985;Lichbach,1990)和那些边缘化团体——诸如农民(Popkin,1979;Tong,1992)和拉丁美洲的贫民区的居住者(Portes,1972)——的行为进行更可靠的经验性理解。再说,这种思想强化了非正规形式的政治参与和作为总体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之间的联系。
第五部分 合法性和政治能力第27节 小结
在本章中,我对合法性是政治能力的中心以及合法性总与价值相关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合法性进程总是一个持续的、没有终结、不完全的进程,在这一意义上,合法性确实是一个变化不定的现象。这又产生两个主要的结果。
第一,合法性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这点无法改变。有鉴于此,在所有服从政治秩序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尊重并珍视政治秩序这一意义上,政治秩序可以确凿无疑地看成是完全合法的,对此人们无法想象。相反,去判断一些政权比另一些政权更为合法,承认任何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程度都可以看成是真实的,并承认它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波动,这样倒显得更为有用。这告诉我们合法性和政治能力只是一个脆弱不堪、变化无常的“量”(quantity)。
第二,合法性依赖于体现服从和同意的价值,这一事实也加强了合法性的脆弱不堪和变化无常。可能有人会因此试图得出结论说,这一概念过于宽松,以致没有多少分析作用。特殊的价值观念牵涉到不同的国家背景,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很难去度量,这一事实看来会使那些认为合法性概念没有多少分析作用的人的理由更加充分。其实,这一结论过于草率。价值被卷入到合法性问题之中,这加强了这种现象的脆弱性。价值观念在各种不同的背景中都会不同,这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们合法性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形成,这又意味着政权在诱致大众支持时具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我们不是要被它们能够使用的不同策略引入歧途,相反,去鉴定那些策略是否成功,这才是更为重要的,然而策略是否成功是非常明显的。这将我们带入到“落实”这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我并不想轻视政权如何引导出合法性这一问题,只是要简单地指出政府这样做的效率如何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由于本章提出的那些原因,产生同意的情况可以在两个更宽泛的方面得到体现:政权不借助暴力手段进行统治的程度,通过正常渠道处理对政权的挑战的程度。鉴于我们的研究主题是政治能力,我们上面的这种观点是第二章中对权力和暴力加以区分的直接结果,也是我所认为的暴力的持续使用是根本没有政治意义这一观点的结果。最后,在本章中,我对这一主张特别强调:权力的实施牵涉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这说明对政治能力作出的任何定义,必须是明确地针对相互关联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行为。这就是我在本章中努力去做的事情。
第六部分 国家政治能力的度量第28节 制度年龄(1)
先于事实得出理论,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阿瑟·科南·多伊勒《第二个污点》
我在前面两章中对组织年龄和政治合法性进行了探讨。在表述时,我清楚地表明了它们是可以度量的。但是准确处理度量问题的任务依然存在。正如本章中将要显示的那样,政治概念常常被设计成可以度量的,但这并不表明所有可能的经验模糊性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事实恰恰相反。
比如说,人们常认为政治秩序应该追溯到它们建立的那个时期,但这一观念本身并没有去确认那个具体的时间。在很多情况下,明智的人不会争论秩序建立的准确日期,尽管测度的标准是清楚的。与此相似,认为国家领袖职位的代际更替年龄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相对要简单一些,但是这种观点依然没有去解决真正的(与名义上的领袖相反)领袖的认定问题。当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对合法性的度量上时,这一问题更加严重。政权在使自己的合法性最大化时,常用的策略是,对它们使用暴力镇压挑战的事实以及它们自己的挑战的严重情况的详情加以隐瞒。由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政权的这种手段制约了关于合法性的资料的系统搜集。
对这一真正问题的承认非常重要,确实,对研究政治冲突的学者来说,这些问题非常普通。然而,我们不使自己成为这些障碍的牺牲品,这点同样重要。有关事实有时被人为地模糊化(特别是成功地去模糊这些事实)意味着度量不如我们预想的那样精确。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我们必须放弃那些诸如测量合法性程度的种种努力。确实,赞同这一观点就等于是承认,仅仅因为我们要去度量政治挑战,这些隐瞒事实的情况就是不合逻辑、没有来由的。人们预料这些困难将会随着材料的政治敏感性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这种看法终究站不住脚。
即便是对并不精确的度量而言,关于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能力的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是能获取到的。尽管它可能会出错,但我在本章中还是要指出,那些材料可以用来对制度的能力和政治合法性在国家之间进行比较。这些比较包含各个国家的数值的总体排名,但是我自始至终强调,国家政治能力永远是一个“度”的问题。
我在第四章中指出,年龄对政治能力有着直接的影响,这里的年龄有两个关键的部分,第一个指的是制度的实际年龄,第二个指的是领导人的代际更替年龄。我将依次对它们进行分析。
制度的实际年龄
制度的长寿与稳定和政治行为的表现联系在一起(请参Black,1966;Rustow,1967;Huntington,1968;Eckstein,1971)。即便如此,对于如何确认国家制度开始的合适日期,人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两种突出的观点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表6.1布莱克和拉斯托选定的国家的组织年龄的估计
国家 巩固时期(布莱克) 独立时间(拉斯托)
阿根廷 1853-1946 1816
巴西 1850-1930 1822
中国 1905-1949 1775以前
古巴 1898-1959 1901
埃及 1922-1952 1922
法国 1789-1848 1775以前
印度 1919-1947 1947
印度尼西亚1922-19491949
意大利 1805-1871 1775以前
日本 1868-1945 1775以前
尼日利亚 1960- 1960
俄罗斯 1861-1917 1775以前
坦桑尼亚 1961- 1961
英国 1649-1832 1775以前
美国 1776-1865 1776
资料来源:布莱克的数据来自Black,1960,p90-94;
拉斯托的数据来自Rustow,1967,p292-294
布莱克(Black,1966,第三章)认为“现代化领袖的巩固是一个关键的阶段”,现代化领袖的巩固的意思是指,在与新的精英斗争时,传统领袖失去了权力。这些斗争有三个特点。第一,它们包括对“进行现代化决定”的声明,这表现在暴力革命时期,这要么源于传统领袖中的不满不忠因素,要么源于代表新的政治利益的精英。第二,对代表农民利益的制度的决定性的摈弃和废除,从而有利于工业经济的形式。第三,政治权威和政治组织的扩张。现代化领袖巩固的这三个要素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需要一代的时间),而且它们容易产生冲突。 此外,它们这种政治上的巩固必须先于经济和社会转型而存在。
表6.1第二栏的数据显示的是布莱克对选定的国家现代化领袖巩固时间的估计。很明显,在大多数情况下,现代化领袖的巩固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如果完全根据布莱克的判断,英国的现代化领袖巩固的时间最长,达183年,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经历的时间最短,分别为27年28年。在那些较为古老的国家,这一巩固的过程常常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例如中国、法国和俄罗斯),尽管在有些情况下它是以革命作为开始(比如法国和美国),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以革命作为结束(比如中国和俄罗斯)。在新兴国家里,关于摆脱殖民统治的日期,存在着一个相似的模式:我们可以对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这一现代化领袖的进程从独立的时候才开始)和印度、印度尼西亚(这一进程在独立的时候刚好完成)作一下比较。
与布莱克对现代化领袖的形成时间的确认相比,拉斯托(1967)把民族国家建立的时间追溯到它们作为一个拥有主权的政治单位获得独立的时候。在表6.1的第三栏中,他的数据展示了他对国家的同样的解释体系。对新兴国家来说,既然非殖民化的具体日期容易确定,它的过程也相对容易理解。而对老的国家来说,要对它的主权获得的具体时间作出界定相对较为困难,拉斯托认为有二十二个国家(包括表格6.1中列出的六个国家)在1775年前就已经获得独立。
尽管在这个表格中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来,但是,布莱克和拉斯托采用的角度有很多共同之处。确实,当对所有的适用于这两种数字的124个国家进行推算时,在布莱克和拉斯托建立起来的两种指数间的排列对数(rand-ordercorrelation)是0.79(即Spearman提出的ρ)。这个对数的大小是合适的,部分(但非全部)是因为一个国家拿一种指数来衡量是这种极值(extremescore)(高的或低的),那么拿另一指数来衡量也有相似的极值。这样,对大多数次撒哈拉非洲国家来说,两种测量标准指的都是独立的日期。而在另一端,对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而言,用两种分析指数来分析都说明它们的历史是较老的。然而,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即政治主权的获得大大先于布莱克所谓的现代化领袖的巩固而存在。这包括,但不只局限于,发生了主要的政治革命的国家:请看表6.1中提到的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数字。在另一种情况下,独立以较小的幅度先于现代化领袖的巩固而存在(比如阿根廷和巴西)。那么这种差别对组织年龄的度量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提到这一问题,我相信,我们必须回到对作为法律实体的国家和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的区分上来(JacksonandRosberg,1982a)。很明显,作为被理解为法律单位的国家,在近年来它已被证明是非常持久的(也就是说,它们总的一直持续存在,它们的边界也纹丝不动),缺乏政治能力或许是它们最显著的特点,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是同样具有持久性的。一旦我们这样来考虑问题,那么象拉斯托的那些标准就是从法律意义上来界定的,而布莱克采用国家现代化领袖巩固这一进程对国家进行分析,是把国家当成一个政治单位来分析的。
这种区分是重要的,因为作为法律实体的国家具有明显的持久性,但这并不等于它的宪政秩序也有着相同的寿命。在发生了主要的政治革命的国家里,这种情况非常明显,但是在没有发生政治革命的国家,这种情况也同样明显。比如说,尽管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十九世纪初期就已经取得了主权地位,但它们中的大多数此后都经历过相当的政治动荡,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军事政变。它们缺少全方位的政治革命,军事政变又使得宪政进程遭到中断,宪政遭到废除,宪政的软弱无力被一次次成功的军事政变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另一条相似的支脉里,研究六十年代中叶次撒哈拉非洲国家的学者,把独立的日期和宪政秩序开始的日期等同起来,这样做完全是明智的、合理的,然而此后的岁月里,人们发现,它们经历了太多的政治动荡(请参Jackman,1978;JacksonandRosberg,1982b;LondreganandPoole,1990)以及宪政秩序的废除。
这种图景告诉我们,国际法中认可的作为法律实体的国家,不应该和体现一定政治能力的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简单地等同起来。另一方面,前者又是后者的前提条件,这样去理解非常重要,而且两个维度(dimension)上的寿命,需要在对国家政治能力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去加以考虑。特别的是,在对最近都经历了政治动乱的两个国家进行比较之时,人们有很多理由相信,那个法律意义上更为悠久的国家拥有着更多的政治能力(当然,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能力都要比在法律意义上和宪政意义上都长寿的第三国少些)。
第六部分 国家政治能力的度量第29节 制度年龄(2)
正如许多人指出的,对在两个方面都很年轻的国家来说,问题是它们必须同时面对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和政治制度建立的进程问题(请参Rustow,1967;Linz,1978)。用韦纳的话来说(Weiner,1965),这一进程包括领土统一和政治整合两方面的任务,这两大问题的同时并存降低了成功完成任何一个任务的可能性。1947年巴基斯坦的建立和次撒哈拉非洲的许多国家独立后发生的事情,常常被用来解释这一进程必须同时解决两大任务这一问题。
相反,在早期的发达国家里,它们作为法律单位的国家早在政治整合问题出现和解决之前就遇到了领土统一问题,并且领土问题已大部分得到解决(但永远不会是完全、彻底地解决)。这两大问题的分离使得问题解决的可能性得到增加。与此同时,法律国家的巩固有助于该民族形成一种共同的民族历史的认同感,而这种共同的认同感在政治合法性的产生中是一个关键的象征性的要素,这一点,我在第五章中已经有所论述。
我还要不厌其烦地指出,随着法律意义上国家的建立,官僚秩序也慢慢地、逐渐地出现了,这种官僚秩序可能坚持采用某种形式,即使国家明显面临着重大的政治转型。这为那些法律意义上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的政治行动提供了适当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在新兴国家里是缺乏的。这样,包括暂时取消和取代宪政在内的动乱对老的国家的影响要比对法律意义上最为年轻的国家的影响轻微得多。
韦伯在早先就指出了这一点,他坚持认为,“官僚制度一旦充分地建立起来,那它就是所有社会结构里头最难摧毁的东西”(Weber,1946,p228)。但是官僚制度即使没有充分地建立起来,它也会持续存在。韦伯继续论述道:
第一帝国后,在法国不管领导人发生什么改变,但权力机器一直以基本相同的形式保留下去。在新出现的权威强有力地建立起来这一意义上,这一权力机器使得“革命”越来越不可能……法国以一种典范式的形式,来展示如何以军事政变代替“革命”:这就等于是说,法国所有成功的转型都是通过军事政变来达成的(Weber,1946,p230)。
西格弗雷德(Siegfried,1956)在描述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不稳定中
的稳定”(stableinstability)时,有着类似的观点。这一标签不是要用来指代某种悖论,毋宁说是要表明,即便内阁政治明显不稳定,象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但是保留着相当程度的人事连续性,无论是在内阁层次上还是在公共服务的层次上都是如此。因此说动荡中有稳定。维利茨(Veliz)在对拉丁美洲进行研究时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尽管对于拉美国家来说,政治长期动荡不安,军事政变和取消宪政是家常便饭,但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得以存活下来,并得到不断发展,即使在人们普遍认为应该尽可能地降低国家的作用的时期里,也是如此。“也许除了古巴是个有争议性的例外,建立了官僚制度的任何地区都没有消灭官僚制度,从而能证明韦伯的观点是错误的”(Veliz,1980,p288)。
但是,这里没有任何一点可以用来说明,政治动乱和宪政秩序的取缔对政治秩序的能力问题无关紧要。相反我认为,在那些经历过那种动荡的国家里,对法律意义上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而言,那些经历对它们的行动能力的影响要小些。与此同时,那些动荡对所有的国家来说都会产生重要后果。这表明,对民族国家实际年龄的度量应该包含两个反映它们的年龄的组成部分,即法律实体意义上的实际年龄和宪政政治意义上的实际年龄。
测量法律实体意义上的国家的实际年龄,我采用拉斯托的新颖的观点(Rustow,1967,p292-293)。如果按照他的观点,那些在1775年之前就已取得政治主权的国家被单独看成是一个团体,并且好象1775年就是它们取得独立的时间。这种做法建立在“前头的几年(或几十年)对于评估制度的寿命是最为重要的时间段”这一假设的基础上,这一点我在第四章后面的内容里已经讨论过。现在我要回到下面的这一问题。 对那些在1776年到1966年(拉斯托研究期限的最后一年)之间取得独立的国家,我一般采用拉斯托的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权中断的几个西欧国家不在考虑之列。巴尔干地区的几个主权遭到更长中断的国家却在考虑之列。对在1967年至1985年间获得主权的前殖民地国家的度量弥补了拉斯托研究的不足。
正如许多人注意到的,法律意义上历史较长的国家相对稳定,而且在当今都得到明确地界定。连同我对它们时下的主权中断加以忽略这一事实一起,这意味着,多数情况下,准确地确定那些国家的年龄是较为容易的。但是还有一些令人烦恼的例子。例如,拉斯托认为德国和意大利在1775年之前就已获得独立。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观点是合理的,但是它们的统一却是此后很久的事情。即使我的修正没有处理好德国在1949年和1990年间分裂提出的问题,我仍然从它们完成统一的时间开始算起。
这带来了这样一个更具一般性的问题,即如何最佳地处理分析单位的变化。按照正常做法,我应把巴基斯坦的独立日期确定为1947年。但是孟加拉国在1972年的建立,使得巴基斯坦的领土界定经历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而且巴基斯坦国失去了一大半人口。类似,越南的实际年龄也多少有点不明确。人们可以把越南作为法国印度支那殖民地的时期和接下来的美国对它的军事干预时期作为当今越南主权的中断计算在内,但是,这样又不可接受地扩大了“当今”一词的通常含义。另外,人们可以把当今的越南追溯到胡志明建立的北越。这等于是承认北越的军事胜利,但是也因而忽略了越南在1975年它的人口和领土几乎增加了一倍这一因素。
最后,正如我在第四章开头提到的,国家的法律地位意味着,它至少得到大部分的国际共同体的承认。出于对1980年创立并为它国承认的津巴布韦的偏爱,我没有考虑1965年罗得西亚 白人少数政权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单边独立宣言”。如果考虑到台湾在1949年前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这点,那么台湾的问题更为复杂。这里的麻烦在于在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对话之后,台湾就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
这些充满着领土和主权的争端的例子提醒我们,尽管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我们的分析单位)在近年来轮廓相对清晰,但依然保留有定义上的不确定性问题。此外,这些国家得到广泛的承认,是因为它们的争端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这个问题。对于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来说,估测它们取得主权的时间要相对简单些。
我对当前的政治秩序年龄的数值——或者用杰克逊和罗斯伯格的话来说,经验上的国家的年龄(Jackson,Rosberg,1982a)——是指在1985年年底前宪政形式被有效推行的那个年份。这个变量的意义和哈德森推测的在1970年之前推行宪政的年龄数据的意义相似(TaylorandHudson,1972)。在那些没有任何宪政形式被正式地采纳的事例中,先前的宪法就已被明确地中断,这时,它的年龄数值是指,在1985年年底前,有效采用不受宪法控制的统治形式的年份。
在多数情况下用第一个变量来确定当前的制度何时开始具有效率,这并不是复杂的事情,但是对有些情况而言,则需要更多的判断力。毕竟它们体现出来的程序和体制是在不断修正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问题是,要把支配政治行为的规则的根本变化和次要的调整区别开来,是要明确最后的一项根本变化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效。
我采用的一般性的规则能够区分出那些——比如,一个新的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建立了,或者早先的政治规则被推翻或中断——根本性的变化。在第一种情况下,法律意义上的国家的年龄和现实意义上的国家年龄是一致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对宪政秩序的废除常常是经由成功的革命或军事政变体现出来的(请记住军事政变的准确所指是指对现状的打击)。这种变化之所以是根本性的变化,是因为与通过对宪政的不断调整而达到的渐进的、正常的演化相比,在中断旧有政治秩序上,它们具有相对的突然性。这里使用的分类规则在下面的事例中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49年建立起来的,它的第一部宪法是在1954年实行的。在此后的岁月里,先后颁布了三部新宪法(分别是在1975,1978,1983年宪法)。尽管最近的宪法有了几个主要的变化,但是没有一个宪法能象1954年宪法那样被看成是对过去的根本性的变化和对过去的突然决裂。这样,当今(到1985年为止)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起点就被确定在1954年。1983年南非共和国的一部新宪法得到通过。然而,新宪法的不同并不能看成是对1961年宪法的根本性的修正。反过来,1961年宪法也只是体现了南非脱离英联邦后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因此我把1910年作为南非新的政治秩序的起点。最后,铁托政府下的南斯拉夫共和国宪法在1946年生效。此后先后制定了三部新的宪法(即1953,1963,1974年的宪法),但是既然南斯拉夫的根本性的变化通过1946年的宪法体现出来,那么南斯拉夫在1985年前的新政治的起点就是1946年。
相反,希腊是在1967-1974年间的军人政权倒台后才采用新的宪法,即1975年宪法。既然1967年的军事政变是对1952年宪法的明确中断,那么当今希腊的宪政形式就应该从1975年开始算起。由于类似的原因,阿根廷和西班牙实行宪政的时间分别应该从1983年和1978年开始算起。在1961年朴正熙在韩国成功地进行了一场军事政变。在他的统治结束之后(1979年他被暗杀时始),韩国在1980年颁布了一部新的宪法,1980年也被当成是韩国采用当前政治形式的起点。在1985年六月,乌干达政府的一些人成功地策划了一场政变。尽管在同年年底之前没有正式采用新的宪法,但是1985年仍然被看成是在1985年之前(在此后的前面几年里,乌干达政府又推行了一些更新的做法)乌干达新的政治制度生效的起点。
这一一般性的标准能够根据它们的渊源来区分政治剧变。由于外部力量或内战引发的主权的暂时中断,在计算宪政年龄的时候不在考虑之列。但是内部因素导致的政治秩序的暴力性中断却是将政治钟表重新拨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并因而被看成是新的政治时代的开始。
我在附录中对国家实际年龄和在1985年之前作为民族国家的年龄作出了评估。我把对这两种年龄的测量放在对代际更替年龄的分析之后。
第六部分 国家政治能力的度量第30节 国家政治领袖的代际更替年龄(1)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实际年龄只是给我们展示了一部分图景,对组织年龄的度量还应该包括对最高领袖职位的实质进行分析。这里的特定的问题是,领导职位是否是个人第一、制度第二,或者是制度程序是否居于首位的问题?要评估这一进程,我们需要对领袖职位的继承问题——由于某种原因(这些原因,我在第四章中已经分析过),这一问题在新兴国家尤为重要——进行集中研究。
让我们来看看两个在当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实际年龄但代际更替年龄又不同的国家。在例A(比如古巴)中,没有出现过领袖职位继承的情况,国家的建立者一直执政,而在例B(比如牙买加)中,它已经历了几次相对有序的领袖职位(包括一系列的领袖个人的转变)的转变。我们的观点就是尽管两个国家都有着相同的实际年龄,但是仅仅因为它显示出来的成功的领袖职位的换届,例B就具有更高的政治能力(或制度体系)。从操作的层次上说,这提出了三个问题:领袖职位的换届次数的估测是指哪个时期的事情;哪些领袖应该计算在内;如何计算多次连任的公职人员?
第一个问题,对领袖职位换届次数的计算应该限定在宪政时期范围内。如果我们关心的是宪政时期内的领袖换届,那么相关的数字是从宪政时期开始时到最近阶段的领袖职位继承的次数。如果我们对此前的领袖职位继承问题感兴趣,那么我们应该把那个时期内的领袖换届的次数也计算在内。换言之,我们必须把不符宪法的革命或政变的领袖换届排除在外,因为这些情况体现的是政治剧变和制度崩溃,而它意味着领袖继承的时钟重新拨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在这一剧变之后,重要的问题是那些推翻了旧秩序的领袖个人能否缔造一个新的政治秩序。我们是在领袖职位继承必须相对有序这一意义基础上来对代际更替年龄进行判断。
第二个问题是哪些领袖应该计算在内?大体来说,答案是直观明了的:我们应该把掌管最高权力的单一的个人包括进去。这一标准使我们的分析对准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总统制下的国家首脑个人。但是还有一些情况,国家首脑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比如说,到1985年底,葛罗米柯(Gromyko)作为前苏联国家首脑(部长会议主席)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远远不及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这种情况还在其他许多国家存在。与此相似,在议会制国家,首相(总理)比国家元首(总统或国王)就更具影响力。很明显,最高政治领袖(国家元首)这一职位的称号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都有不同。因此在测量领袖职位换届的次数时,首先对相关的职位进行区分,然后对担任这一职位的个人加以确定,就变得非常重要。
最后,我已经对担任领袖职位的个人的数量作过强调,而没有对担任这一职位的任期进行强调。担任这一职位超过一届任期的领袖个人只计算一次,不管任期是否属于连任。在其他的情况下,不管内阁是否变动,这种程序在制度上体现了最高政治领袖职位的连续性,比如战后的意大利就是这样。
在附录里,我对各国国家领袖的代际更替年龄评估情况进行了陈列。这些数字确定了每个国家在当今的宪政时期里——它是指从当前的宪政安排(或宪政外的安排)开始到1985年底这段时间——担任最高政治职位的领袖个人的数量。
制度年龄数据的特征
表6.2是对附录中的国家评估的总结概括,它展现了三种标准的每一种的测量范围和方式。 这些数字明显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点。
表6.2对1985年前民族国家年龄度量的简要的统计数字
到1985年止获得独立的时间(年) 到1985年止颁行宪法的时间(年) 从颁行宪法开始的国家领袖的数字(人)
最小值 6 1 1
最大值 211 199 61
平均值 83.2 31.3 5.1
中位数 43.0 20.5 2.0
偏斜度 0.76 2.49 3.39
国家数 134 134 133
首先,大多数民族国家是非常年轻的。几乎在所有的例子中,法律年龄都超过了它的宪政形式的制度年龄,但是即便如此,那些民族国家是年轻的,这点都毫无疑问。从某一意义上来说,战后非殖民化步伐的加大和与之相伴生的主权国家绝对数字的扩大,这非常正常。但是它们宪政年龄年轻也是惊人的,即使对上一世纪就获得独立的许多国家而言,也是如此。既然对最高政治领袖的代际更替年龄的度量限定在当前的宪政时期,那么大多数国家的代际更替年龄也应该是同样非常年轻的,而且,它们确实如此。领袖的数目在1到61的范围之间,而中位数仅仅是2.0。
表6.3根据财富确定的到1985年止的124个民族国家的年龄的中位数
从独立开始计算的时间(年) 从颁行宪法开始算起的时间(年) 国家领袖的数量
低收入经济数量:36 26 11.0 1.0
中下收入经济数量:36 43 11.5 1.0
中上收入的经济数量:21 76 16.0 2.0
东欧非市场经济数量:10 76 38.0 2.5
工业化市场经济数量:21 155 112.0 19.0
注:我除了把高收入的石油输出国划归到“中上收入经济”中去之外,这些国家的这种组合都是按照世界银行对收入水平的划分得来的。
第六部分 国家政治能力的度量第31节 国家政治领袖的代际更替年龄(2)
第二,对三个度量标准而言,国家评估的布局严重地向右倾斜。这样,所有的平均值都要大于它们的中位数,而且对偏斜度的度量也是容易的。当然,偏斜度与更新倾向是一致的,特别是与宪政年龄一致。它还表明,人们对低分值国家之间的差别比高分值国家之间的差别更感兴趣。正如我在第四章末尾处指出的,既然前面的几年或者领袖个人是制度化最为关键的东西,那么人们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组织年龄的增加,组织的更新倾向的程度也会随之下降。连同附录中国家评估的明显布局一起,这意味着低分值国家间的差异应该在分量上超过高分值国家间的差异。我们最容易通过检测民族国家组织年龄的对数(而不是通过原始数字)来获得这一结果。
当我们从财富和地理区域来考察组织年龄的差异时,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又会得到一种新的观点。表6.3展现的是根据国家财富得到的关于三个标准的年龄中位数,这些国家财富数字是根据世界银行1987年对各国1985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统计划分得来的。对每一个标准而言,在财富和年龄之间都有着一种明显的单一性的关系。如果把年龄当作评判标准,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政治能力要比其他国家的政治能力大得多。确实,差距的幅度从表6.3的第一列到第三列在不断增加,这样工业化国家和其他所有国家的代际更替年龄的差别是巨大的。
把工业化国家搁置在一边,表6.4展示了根据地理区域划分的第三世界
表6.4到1985年止据地理区域划分的一百个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年龄的中位数
从独立后开始算起的时间(年) 从宪法颁行开始算起的时间(年) 国家领袖的数量
亚洲数量:21 39 15.5 2.0
拉丁美洲数量:24 152 16.5 2.0
中东、北非数量:18 39 15.5 1.5
次撒哈拉非洲数量:37 26 11.0 1.0
注:这些数字不包括表6.3中的东欧非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市场经济的类型的国家,
还有希腊、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葡萄牙和南斯拉夫也没有包括在内。
国家组织年龄的中位数。第一栏中从独立后开始算起的时间数字反映了非殖民化的图景,即拉丁美洲国家首先获得独立,而次撒哈拉非洲国家是最后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的平均时间是1960年)。表中第二栏和第三栏的数字表明,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年龄的差异并没有直接转化成宪政年龄和代
表6.5到1985年止与财富和地理区域相关的民族国家年龄的回归系数
(国家个数:122)
因变量 从独立后开始算起的时间 从宪法颁行开始算起的时间 国家领袖的数量
人均能源消耗对数(1985年) -0.3 0.34*﹡ 0.22*﹡
(0.06) (0.08) (0.07)
亚洲 -1.06* -0.35 -0.96*﹡
(0.23) (0.33) (0.28)
拉丁美洲 0.06 -1.04*﹡ -1.07*﹡
(0.21) (0.29) (0.25)
中东、北非 -1.05*﹡ -1.00*﹡ -1.29*﹡
(0.21) (0.30) (0.25)
次撒哈拉非洲 -1.67*﹡ -0.50 -1.15*﹡
(0.26) (0.37) (0.31)
恒量 5.07*﹡ 1.18 0.32
(0.48) (0.67) (0.57)
R2(样本决定系数) 0.53 0.45 0.53
限制性的样本决定系数(仅指能源消耗)R2 0.23 0.35 0.42
注:对每个回归而言,因变量已转换成对数。表中的主要项目是采用公制的回归系数,回归系数下的圆括号里的数字是它们的标准误差。标注了星号的系数是它们的标准误差的三倍。除了乍得和莱索托这两个例外之外(对它们而言,能源消耗率是不适用的),这些估计值建立在表6.3的数字的基础上。这样,地区效应就体现了表中的地区和非第三世界国家在净能源消耗率上的差异。
际周期年龄的差别。尽管次撒哈拉非洲国家的宪政年龄多少比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的宪政年龄要小,但是这种差别并不明显。此外,最后一栏的数字表明,并不存在象在宪政时期国家政治领袖体现的那种代际更替年龄的地区之间总体性的差别。
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表6.3和表6.4中的数字忽略了地理区域和国民财富之间的联系。表6.5相应地报告了三种政治年龄的关于财富和地区的回归数值,其中在表6.4中对地理区域作出了划分,财富是根据1985年的人均能量消耗率来测定的。 这种回归数值反应的并不是一种因果关系,相反,它们只是总体上作为对这些数据的概括和简化而表现出来。
在对地理区域加以限定的情况下,表6.5第一列的数字表明在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年龄和财富之间的简单的关联消失了。相反,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年龄反映地区性的差别,次撒哈拉非洲国家属于最年轻的国家集团,亚洲和中东、北非国家处于年龄中间层次的国家集团,而剩余的国家属于最老的国家集团。尽管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系数表明,它们的宪政年龄多少要比人们根据它们的财富预计的宪政年龄要轻,但从宪政年龄的意义上说,它和财富的关联则得以存留。它们的代际更替年龄的估计值也多少有些不同。与表6.4中的原始数字相一致的是,在对财富加以限定的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很少出现地区性的差异,尽管第三世界国家与其他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经历了更少的领袖继承。
这些模型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表明组织年龄(政治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简单的因变量,因此它们不能简单地化约为经济发展。首先,尽管在其间有一种零序关联(zero-orderassociation),但是对系数的测定表明这种关联远非完全:表中最下一行数字浮动幅度是,从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年龄系数的0.23到代际更替年龄系数的0.42。其次,该表揭示了这种关联的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换句话说,我的关于组织年龄重要性的观点不是对这一观点——政治能力是财富的一个未加修饰的“直线发展的”因变量——的一个概括。
随组织年龄特定要素的不同,各地区情况也会不同,这一说法还有一层含义。组织年龄的三个组成部分不能视为是政治能力的三个可相互替换的指示器。法律年龄和宪政年龄、法律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宪政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这三者的相关比分别是0.27;0.42;0.79。
前头两个的相关比值相当低,这强化了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年龄和宪政年龄的差别,这也可以从表6.5中的回归系数的测定中明显看出来。我在前面已经主张法律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在分析上是有差别的,但是对于组织能力的评估却起到关键作用。这种差别在现实中的表现说明,在对国家政治行为进行评估时,需要对组织年龄的每个组成部分独立的加以考虑。
与此相对的是,第三个相关比值要高得多。这主要源于代际更替年龄标准的建立,因为它表明了在当今的宪政时期内的领袖的个数。这一设计明显地使它们的这一相互关系成为度量年龄的其中的一个标准,尤其对于那些实行老宪法的国家来说更为如此。即便如此,这一相关比也是不完善的。最为突出的是,这一相关比值掩盖了实际年龄较轻国家之间的宪政年龄的巨大不同。考虑到最年轻的国家也是最脆弱的国家这一点,这两种标准的不相一致说明,在最为重要的国家评估值的范围里,它们是对制度年龄的不同方面加以确认。而且这种不一致在表6.5第二和第三列的回归值中明显地体现出来。
第六部分 国家政治能力的度量第32节 合法性(1)
在本书不同的地方,我都认为合法性的分析是要研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实质。因此,检测两个集团的行为就是问题的关键。在将这点牢记在心之后,我在第五章中提出政治合法性有两个关键组成部分的观点:权威依赖于物质强制手段的程度如何,在什么情况下挑战者会使用暴力手段来发展自己的利益?
物质暴力的官方使用
对国家和政府镇压挑战的方式进行的研究在近十年来大幅增长。象大赦国际、自由之家、美国国务院等形形色色的组织都经常收集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政府外的组织动员大家对政府的强制手段进行监督,以发挥它们的看门狗的作用。这些资料有时候就是从那些政府外的组织产生的。但在其他时候,这些资料还是从政府决策过程中产生出来。随着卡特政府在七十年代末对人权问题的重视,人们对政府实行强制手段问题的关注也大大加强了。
我对物质暴力使用的重视在很多方面与这类似,但是我不是从人权关怀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的。这种考虑对于眼前的意图来说显得过于宽泛,而且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权力的使用上移开。例如,在1947年为联合国认可的《普遍人权宣言》中(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就对保障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食物、衣服、住房、医疗等物资的供给和对政治权利一样加以强调。当然,这些是重要的和有趣的问题,但是它们对眼前的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即便我们把注意力限定在物质暴力的使用上,我的观点也与下面的政治权利指向的定位有区别。手段合法(legality)的问题与对权利的任何评估都有关系,所有的政权都可以依法使用暴力,尽管依法使用暴力的程度并不一样。相应地,军事管制的实施和对政治反对者的拘禁也常常被视为是合法的,而且有关“安全”的法令也被用来支持关于采取这种行动的声明。这种声明是否被广泛地认可和接受当然是另一回事。但是谁在这一点上不清楚,谁的安全就存在问题并有待解决。然而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这种理由长期有效,那么政治权利被侵犯就变得不明确了,即使使用了暴力,也是如此。相反,政府暴力行为合法的问题对在权力框架(我采用的)内使用暴力的解释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官方使用暴力,不管它们有任何充足的合法理由,暴力使用这一事实都将直接反映权力的丧失(并削弱了政治能力)。这样,我的视角和人权视角区分开来了。
测定官方使用暴力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人们关注的可能是国家镇压机器的规模,并要么通过计算国内安全力量支出的大小、要么通过计算那些武装力量的大小(从人数的意义上)来得出关于官方使用暴力的数据。这里的假设是,拥有更大国内安全力量的国家(按人口比例)更加依赖于那些武装力量。然而这种观点有很多地方需要指出,它在区分对内和对外安全预算和人员配备时,有很大的实际困难。比如说,尽管军事管制法的实施的理由是要最大程度地扩大国内安全,但是军事管制法本身是由军队来实施的,而军队公开声明的目的是要抵御对国家的任何外部威胁。由于政权常常把维护国内安全作为对挑战者使用物质暴力的遮羞布,声称国内秩序的挑战者是国外势力的代理人并以此为借口来镇压他们,这样国内/国外的区分就变得并不清晰了。 这和政治信息的敏感性一起使得相关的资料很难获得。
但即便没有信息获取和界定上的问题,度量国内安全力量规模的手段也永远不是一个完善的方法,因为国内安全力量的大小并不直接意味着对暴力和那些力量的使用。相反,假定规模的大小能够体现力量的大小,并且不管效率的问题,大规模的国内安全力量充其量只是表明政府有运用暴力的倾向和偏好。
作为测量官方使用暴力的另一种方法,可能会有人把国家的定性判断改造为对国家的差别进行层次排列。或许运用这种方法的最杰出的代表作是自由之家对评估数字的汇编(Gastil,1985),这一汇编包括了政治自由(比如说,政治表达自由和政治组织自由)的测评得分。尽管这一系列与政治合法性相比,它更多的与自由民主的实施有关,但这类资料从根本上看来,要比第一种方法提供了更多有关镇压的明确数据。然而,实际困难依然存在。在加斯蒂尔(Gastil)提供的资料这一特殊例子中,排序标准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且许多国家得分定性判断的基础也不明确(Bollen,1986)。更为普遍的是,考虑到它们依赖于一个天生模糊的定性判断基础,要减轻资料的这种形式的问题也不容易。 把这些问题搁置在一边,类似加斯蒂尔的得分还是不能直接反映暴力的使用。
在世界优先组织(WorldPriorities)汇编的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对公民的官方使用暴力的年鉴中(Sivard,1986,p24-25),我们可以获得很多与这一问题更直接相关的信息。这一年鉴划定的暴力行为的类型有:拷打、酷刑、暗杀和政治屠杀。这些分类是根据诸如大赦国际、华盛顿拉丁美洲局、美洲观察等组织的出版物和资料汇编、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国家人权状况报告》和人权因特网(Sivard,1986,p42)得来的。尽管这些资料的覆盖面较广,但划归在官方暴力条目下的各种行为没有明确地予以界定这一事实制约了度量的价值。此外,它们仅把官方暴力分为“没有使用(none)”、“偶尔使用(some)”、“经常使用(frequent)”三个等级,而且把国家划归某一特定类型的标准有时也多少有些模糊不清。
鉴于这些困难,最有前途的方法是那些集中关注官方使用暴力的事情。这一方法并不能解决度量中的实际障碍,这点我将在下面加以分析。但是因为这一方法对政府使用暴力的场合和那些不使用暴力(不管有什么原因)的场合作出了区分,在所有的方法当中,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最坚实的基础。
在暴力的使用上,政府有着可供自己支配的广泛选择。宣布戒严是我提到过的其中一种选择。它还常常可以为戒严而采取很多更为特别的行动,并为那些行动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不是因合法性而加以认可和接受),使这些行动变得合理化。在这些行动中,宣布戒严或许是一种最为宽容的手段。但是也有这样一种情况,暴力的使用并不要求宣布总体戒严,尤其是当政府针对的目标是特定的集团而不是针对所有公民。在针对特定反对集团的特定地区可以实行宵禁。即便更小的团体或个人也可以是宵禁针对的目标,在这一情况下,在某一指定地区实行宵禁并没有任何效果。相反,或者政治犯常常被逮捕,或者反对者被流放,或者报刊杂志被关闭,这些手段都是单一地得到使用的,政府并不采取其他更具一般性的行动。
政权可供选择的手段的广泛性意味着,人们可以把它当作物质暴力使用证据的这些行动必定是混杂不堪、多种多样。目标集团的大小规模也有很大的不同。针对挑战者使用的有效手段(先发制人或者后发制人)的范围也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在其他一些独立的环境中,这种多样性也可能是关注的根源。比如说,如果人们对特定国家的一系列事件的发展轨迹感兴趣,那么特定行动的目标、它们何以成为目标、或者行动的结果都会成为他们重要的考虑因素。这样一种对事情发展脉络的分析,可能也要求把注意的焦点限定在更具同一性的一系列的事件上。但是不管它们的内在意义如何,也不管它们对其他分析的关注有何影响,在评估一个政权的总体的合法性上,这一问题终究是次要的问题。在任何这样一种对合法性的评估中,问题不是在某一情况下政府为什么会决定使用暴力,或者对发起者而言,那个行动是如何的行之有效的。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政府和它们的代理人是否,并在何种程度上确实每隔一段时间就使用物质暴力,以便能够根据它们对镇压的普遍依赖来对它们进行比较。
有关国家使用物质压制手段频率的最为全面的资料是《世界政治和社会手册,WorldHandbookofPoliticalandSocialIndicators》(TaylorandJodice,1983,2:61-77)。在“国家强制行为”这一项目中,这一手册列出了“政府制裁”的特征,这些特征能够界定什么是对个人和机构的审查、对政治活动的一般限制,和其他的对社会和政治行为的限制。
审查包含政府对包括新闻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的限制、约束或恐吓行为。这种行为的典型例子是关闭报纸杂志,或者对国内发表的文章或发往国外的信件予以审查……对政治行为的限制包括政府的一般性的限制措施,比如说宣布戒严,针对国内安全的军事调动、实行宵禁。还包括专门针对个人、党派或其他政治组织的行动。这些特定行动包括政府对那些有不同政治信仰和行动的人的谋杀,对政党的取缔、或针对政党的骚扰活动,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对反对派领袖的拘捕、对因进行了不利于国家利益的政治活动或表达了不利于国家利益的反对意见的个人的流放或驱逐出境行为、对从事了包括示威、暴乱、政治罢工、武装进攻或暗杀行为等等政治抗议活动的人实行拘捕或放逐。最后,对政治行为的限制还包括政府对外国间谍采取的行动(TaylorandJodice,1983,2:62-63)。
因为这些措施属于国家的强制行为,因此它们只是指那些由政府的正式
机构发起的事情。这样,象黎巴嫩那种情况,从1975年开始就很少有中央权威,由不同的私人武装和受国外支持的军队采取的强制行动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尽管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行刑队与政府部门有着明显的联系,但它们的行动也适用于上面的考虑,不能看作是国家的暴力强制,因为它们并不成为官方代理人。
除了对政府的强制的信息进行研究以外,泰勒和乔迪斯还(TaylorandJodice)对政治处死专门进行了分析。
政治处死是这样一种情况,在国家权威的命令下,个人或团体在拘禁时就被处死。人们在暴乱、武装进攻、政治罢工中被杀,还有暗杀——即便是由政府策划,都应该排除在外。对刑事罪犯比如杀人犯执行的死刑也应排除在外,因为它们没有政治意义。典型的是,政治处死是这样一种处罚:那些被处死的人是被指控犯有威胁国家、政治制度、政权或领袖地位安全罪的人(TaylorandJodice,1983,2:63)。
泰勒和乔迪斯看到,政治处死是由国家权威直接或间接挑动的,这一要求有时候给归类带来了实际的困难。例如,他们注意到史蒂芬·彼科(StevenBiko)死在南非的监狱里,没有正式的法庭宣判和行刑。尽管如此,但由于以下理由,这一事情仍然被看成是政治处死。
对南非安全机构及其行为的舆论气氛足以决定这一事情决非偶然。国家政治领导层的观念和期望的苗头能够鼓励或阻止对政治犯人进行这种处理。在南非,并且在其他许多威权政体中,证明自己并非同谋这一任务是各国政府的负担。国家领袖对以他们的名义实行的行动负有政治的和道义的责任,即便他们并没有颁发这一特殊的处死命令(TaylorandJodice,1983,2:63-72)。
就地理覆盖区域和时间覆盖范围而言,《世界手册》算得上是一部现存的
资料最为详实、全面的集子。它包括了世界上140个国家从1948年到1982年的整整三十五年的信息。 从全书看来,我们可以得到每个国家两个方面的资料。第一种资料是对政治事件每日进行统计,第二种资料是对政治事件进行年度统计。由于年度资料有利于抹平官方使用物质强制手段的短暂波动,年度统计基础上的资料更为明确,也更为可取。
我在本章的这一部分自始至终认为,我们必须关注政治处死命令数量上的重要差别。我已经指出我们应该更为强调低值国家之间的差别,而对高值国家的差别在重视的程度上打个折扣。比如说,政治处死案例从零个到十个和从五十个到一百个的政治意义决不一样,即便两种情况的数字都是原来数字的两倍。零次政治处死和十次政治处死的区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跨越了从无到有的门槛。而政治处死从五十次发展到一百次对牵涉到的个人来讲当然意义深刻,五十这一数值表明,政权已经大量地使用暴力手段了。鉴于这些原因,政府制裁最具解释力的方法是运用自然对数对原始数字进行评估。 正如我在本章早先指出的,这种数据转换保留了原始的排列次序,但是能够更为突出低值国家间差别的意义,并弱化高值国家之间差别的意义。
我将在后头对这些多种多样的数据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现在,我要转向如何测定对国家的挑战的严重程度这一问题。
第六部分 国家政治能力的度量第33节 合法性(2)
暴力挑战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对国内政治冲突的经验比较性的研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请参这两本杰出的著作,e.g.,Gurr,1970;Hibbs,1973)。尽管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解释方法,但是他们的研究都把理解在什么条件下权威的挑战者会使用暴力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这样,格尔(Gurr)就把他的著作的标题定为《人们为何造反》(WhyMenRebel)。此外,这些研究还对暴力挑战的测定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从中我们能够汲取到有益的营养。
希布兹(Hibbs)认为,要把某些行动视为对权威的挑战,这些行动必须满足三个相关的条件。第一,这些行动必须具备反体制的实质,必须是反政府的抗议,但是支持政府的游行不能算是对政府的挑战。第二,它们必须具有明确的、直接的政治重要性,以致它们的威胁最少给政治精英的规范地、正式地运行带来严重的麻烦和不便。这一标准把普通的劳工罢工排除在外,但是那些最少具有威胁性的、温和的政治目标的罢工被包括在内。第三,这些行为必须是集体性的行动,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把谋杀和武装抢劫之类的犯罪活动排除在外(1973,p7)。
希布兹在运用这一标准来对一百个国家在1948年到1967年这段时间的数据进行维度性(dimensional)分析时,他得出结论说,大众政治暴力有两个一般性的组成部分:集体抗议和国内斗争。集体抗议反映了暴力的更为温和的程度,包括反政府示威、政治罢工和暴乱。国内斗争是指一种逐步升级的形式,包括政治暴力、武装进攻和政治暗杀。既然国内斗争更为明确地表明了对政权发动的暴力挑战的不同的严重程度,那么它看起来是一个更为适合于正在考虑的目的的组成部分。
即便如此,希布兹确认的所有三个变量对国内斗争问题有相同的影响,这也不确切。正如希布兹(Hibbs,1973,p11)自己指出的,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反对那种把暗杀置于“大众暴力”这一项目下的观点。即使最乐观的看,关于暗杀的政治意义、反体制的特征和它的集体性也是不明确的(TaylorandJodice,1983,2:43),这意味着它们不必满足要包括进去必须具备的三个指定的标准。我相信对类似“武装进攻”的事件的解释也是模糊的,而且,希布兹的经验性结果表明,那些事件确实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国内斗争这一维度。
这些考虑表明,对暴力或挑战严重性的度量,它的最好的单一的变量只能是政治暴力的死亡人数。这一方法至少有三个优点。第一,单一变量比复合变量更具有解释力。死亡人数的统计更不易于变得模糊起来(上文分析的),因为它们体现了集体事件的严重程度和明确的政治意义。虽然死亡人数中有些人是死于集团间的暴力,但他们的大多数是因官方或非官方的政府代理人而死。 其次,如果我们把暴力挑战想象成一种对参与者来讲具有很高潜在成本的行动,那么死亡人数是实际支付成本中的最直接有效的数字。最后,从更为现实的意义上来说,有各种证据表明,因为死亡人数的可见性,它们比其他在希布兹看来更为特别的事件(比如暴乱和武装进攻等等)更具有新闻价值。因此它们常常得到更为完全的报道(关于这点,尤其请参SnyderandKelly,1977;Rosenblum,1981;Weede,1981)。
正如国家物质强制的情况一样,《世界政治和社会手册》也是一部关于国内政治暴力死亡人数资料最为详实、全面的集子(TaylorandJodice,1983,2:48-51)。这些死亡人数的数字是指在包括抗议、暴乱和武装进攻等各种不同的特殊事件中的死亡人数。“范围包括在外国对本国进行干涉中死亡的国民的人数,但是不包括外国人的死亡数字。也不包括政治处死的死亡人数,不包括死在敌人监狱里、国际冲突中和边界冲突中、以及杀人犯的牺牲者的死亡人数”(TaylorandJodice,1983,2:43)。我们可以从中得到140个国家在从1948到1982年三十五年时间跨度里的有关信息。
与我对有关国家强制资料的处理一样,这些有关挑战严重程度的国家原始数据最好是转换成自然对数值。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这种转换使得国家评估值的增加的意义有所降低。例如,报道的六十年代尼日利亚内战伤亡数字要比报道的印度尼西亚内战伤亡数字大,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死亡数字在两个国家都是巨大的。
第六部分 国家政治能力的度量第34节 合法性(3)
有关合法性数字的特征
这些数据如何很好地反映官方的暴力使用和对权威挑战的严重程度呢?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估价时,需要首先处理其他几个问题。我认为,可靠性(reliability)和有效性(validity)的问题,数字集成的问题,可能的资料标准化的问题,都是需要首先加以解决的问题。
《世界手册》一书的汇编者对他们收集的资料的可靠性予以了很大的关注。确实,他们对这点的关注堪称典范(尤其请参TaylorandJodice,1983,2,chap.1and6)。关于每个国家的信息都有两个来源渠道,纽约时报(NewYorkTimes)和第二个渠道(有可能,这一渠道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性的渠道)。充分的事实表明,其他附加性的渠道很少能带来什么新的信息(请参JackmanandBoyd,1979),在这一意义上,编者把上面两个渠道作为获取相关信息的两个主要渠道的做法是有道理的。此外,泰勒和乔迪斯还提供了相当多的有关资料整合可靠性的信息。当然,无论是我还是泰勒他们都不认为这些资料没有误差。但是从它们合理地反映了原始资料中信息的有效性来看,这些资料的可靠性还是很高的。
现在我们转向有效性的问题。这些资料折射出了报道行为,这也就是说,新闻媒体认为哪些事件和伤亡人数具有新闻价值。即便在没有任何新闻限制的地方,也很明显,新闻媒体会对不同寻常的事件大肆渲染,而对无关紧要的事情轻描淡写。尽管有人会认为这反映了与“好事”相比,新闻媒体对“坏事”有着更为明显的偏好,但是这里头并没有任何神秘性,对资料的有效性而言也不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就象火灾比平常的逛街采购更具新闻价值一样,暗杀比国家预算的小幅度的修订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样,新闻媒体就有各种理由更有可能去报道采访那些更为引人注目、突如其来的事情(Rosenblum,1981)。在这点上,我所用的数字相对较为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源于暴力的死亡人数比相对平缓的抗议更有可能得到报道。与此相似,有很多事实表明,镇压手段的运用也比放松镇压力度更容易得到报道(Rosenblum;TaylorandJodice,1983)。
即便这样,新闻界对不同国家的关注也会在缺乏对新闻界的限制的情况下有所不同。一些国家可能得到新闻界的更多的关注,因为这些国家被认为是更重要或问题更为严重的国家。比如说,1981年后新闻界对萨尔瓦多这样一个小国的报道得到了显著的增加,因为这个国家被认为可能变成另一个越南(TaylorandJodice,1983,2:178-179)。另外还有证据表明,民族政府可能会因为怕面对国际压力而采取措施,以尽可能少地增加新闻报道量(ManheimandAlbritton,1984)。
如果政府掩盖事实并对新闻界进行限制,问题当然会更为严重。这种事情在前苏联和南非那样不同的国家里都是普遍的。在七十年代中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UNESCO)努力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信息秩序”的倡议下,它们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地方获得了尊重,并取得了前进的动力。除了别的一些以外,这一倡议还被倡议和支持它的人说成是要限制西方对国际新闻媒体的控制,要更加重视正面新闻而不是负面新闻。 许多非西方的参与者的怨言被阿格瓦拉(NarinderK.Aggarwala,当时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很好地总结为“信息权利是一个基本的权利,但不是绝对的权利”(出自RichstadandAnderson,1981,xvii)。阿格瓦拉继续论述道:
在各种基本权利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进程正在全世界一直进行下去,而且这在第三世界更为轰轰烈烈,在第三世界里,基本权利的概念是根据每个国家自身的力量——并因而决定自己民族的、历史的和文化的需要——来界定和解释的。尽管新闻界的领袖努力推动新闻的最大限度的自由,但是,在特定国家,新闻享有的自由程度完全取决于该国领袖对国家政治需要和安全需要的看法。这种例子在西方世界照样可以存在。新闻自由在西方不同的国家里同样根据各国自己的历史发展而得到不同的对待。
这种观点的相对主义和权威主义色彩是不言而喻的。领袖考虑国家政治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方式,不可避免地与他们自己继续占据公职的意愿联系在一起。有鉴于此,他们主张改变国际信息旧秩序的目的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很明显,有关合法性的资料是敏感的,并因而难以收集到,而且随着政府掩盖这些资料的努力的增加,难度也将进一步增加。尽管我们对这一困难有所了解,但是困难的存在并不能成为我们草率地放弃这些有效资料的理由。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政府试图掩盖那些有关暴力使用的信息,正是因为那些信息与它们的合法性直接相关。而且,那些关于审查制度的资料在衡量政府制裁和处罚时也应包括在内。尽管那些材料总是有很多地方可以修正,但我认为它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官方和挑战者使用暴力的许多重要信息。
除了有效性和可靠性这两个问题之外,很明显,那些资料是对事件和伤亡人数进行综合和概括的产物。从这种形式的信息中,我们很难得出一个关于暴力使用是由哪些驱动力量促成的推论,同样,我们也无法从中得出一个关于暴力使用的序列(先后次序选择,英文为sequence)的结论。正如斯奈德(Snyder,1978)、蒂利(Tilly,1978)、迪纳多(DeNardo,1985)、里茨巴奇(Lichbach,1987)和其他的人指出的,在有些情况下,这还真是一个制约因素。比如说,那些资料就不能用来分析那些决定使用暴力的人——不管是官方还是挑战者——是如何进行策略计算和考虑的。
但是我关注的问题是,政权或国家总体上的合法性的不同,而不是要考虑与策略——那些使用了暴力手段的人的策略考虑——相关的问题。这样问题就不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中要使用暴力而在那种情况中不使用暴力或在这种情况中是这样使用暴力而在那种情况中却不是这样使用暴力,一句话,问题不是为什么要或如何使用暴力的问题,而是暴力使用程度的问题。综合性的资料必须、也能够对不同的国家在这一思路上进行比较,因为根本性的问题都是按照综合性的标准来看待的。此外,我早先强调过测量暴力使用而非暴力威胁的重要性,因为所有的政府(或国家)都有能力使用暴力。这些资料正体现了对这一点的重视和强调,因为它们讨论的是暴力事件的次数及其伤亡人数。
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资料进行综合。这里有两个问题有关系。第一,我已经指出,对政府使用制裁手段的度量可以通过相对多种多样的事件来进行,这些多种多样的事件除了别的以外,还反映了政府可用的压制手段的不同。但是为了某些目的,区分针对个人的压制(比如逮捕)和针对集团的压制(比如宣布戒严或实行新闻审查),对那些资料进一步加以分解可能会更有帮助。针对个人的压制手段更为零散、孤立、短暂,而针对集团的实行的压制一般更为持久和无休无止。要界定针对集团的压制的起点日期相对简单容易一些,而要界定这一压制的结束日期却较为困难。按照压制的两个基本目标对象,对这两种压制进行区分,这将降低政府制裁度量的混杂性、异质性。 因此而产生的针对个人的系列制裁也将能和政治处死的单一系列区分开来。
第二,我已经指出,年度系列资料要比每日统计的系列资料更为可取,因为后者对短期波动的反应过于敏感。这一观点并不神秘,而且确实有很多学者使用较长的时期来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比如希布兹[1973]就以十年的时间间隔作为一个基本的区间)。然而还有一些人认为,任何一种这样的时间区间都显得过长。比如桑德斯(Sanders,1978,1981)就认为对综合性的资料的时间区间应是一个月的间隔。一旦他以这种区间作为基础来度量,那么就很难产生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分析模式。我不是说任何特定时间区间的综合对任何情况都是最适度的,但是我对桑德斯的主张并不满意。
在选择一个适当的时间区间时,我们首先要明白,过短的时间区间对短期波动的反应会过于敏感,并且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确实,时间区间越短,测量的可靠性也就越低(Allison,1977)。这样,人们就会纷纷议论说,桑德斯的结论无法得出具有一般性的模式。对那些对有关冲突的资料进行研究的人来说,资料综合的时间幅度过长也会降低它的可靠性,而这一点也不奇怪。即便我们对原始资料草草一看,就会发现新闻报纸常常以这样一种普遍的方式来报道日常冲突,并说“估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大约有200个市民在种族冲突中丧生。”这就是《世界手册》上的资料为什么会觉得年度时间区间比日度或月度时间区间(桑德斯使用的)更为可取。
最后,在这点上我是指原始的事件统计数字没有以任何方式加以规范化、标准化。这不是说不应该对它们加以规范化。有时候为了某些目的,对资料一定的修正和规范是有用的。让我们来看看规范的三种方法。
第一,考虑到各民族国家人口规模的广泛的不同,可能有人会认为应该以人口规模的标准来加以规范。更细一点看,自发的人口统计、核对是很难的。对针对集团采取的政府制裁的资料采用这种做法是不值一提的,因为例如宣布戒严之类的事情是典型的针对全体国民,或针对根据地理区域确定的其中的一部分人的。根据人口规模来实行的规范化,在适用针对个人的官方暴力的情况时,也是模糊不清的。1980年利比里亚军事政变后政治处死概括性数字的意义已经改变了,难道它也会以同样的幅度在人口要多得多的尼日利亚出现吗?难道对因参加了政治活动的二十个人实行拘留在新西兰会比在美国认为更具影响吗?这种模糊性在有关国内政治暴力死亡人数的资料上同样是模糊的。尽管在一定的意义上,在暴力中冒死亡风险的人数会随人口规模的加大而加大,但是并不等于说死亡人数的政治意义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而得到增加。这种模糊性阻止我们根据人口规模来对资料加以规范化。在可能有理由把人口规模当成是相关因素的地方,这一变量最好是当成一个其影响可以估测,而非事先就假定它有优先性的、独立的、供控制的变量。
第二,伯仑(Bollen,1980,1986)提出了一个关于度量政府制裁的有趣的问题。这些资料当然包括以新闻审查、宣布戒严等等形式对集团实行的镇压。在一个在这一系列制裁手段实施之前对新闻媒体的限制就已相当严厉的地方,在实行这一系列制裁手段之后,就很难对新闻媒体实行进一步的限制,即使权威倾向于这样做,也不行。与此相似,如果一个处于紧急状态的国家在事先就宣布了戒严,那么事后它再也没有必要接下来实行军事管制。鉴于这种可能性,对官方暴力的使用在有些国家可能会得到低估,除非对它加以修正,伯仑就对这一系列手段进行了修正。 另一种替代性的方法是,把它作为控制性的变量来进行适当的调整,并估测它的影响和效率。尽管任何这种控制性变量的特定实质取决于分析的经验模式的实质,但总体目标还是应该在这一系列资料开头合适的地方把限制的普遍性包括进去。
提到的第三个可能的规范化源于这一观点:因为不同的政治体系有不同的暴力传统,所以不能对暴力事件的原始数字直接进行比较。比如,杜沃尔和夏米尔(DuvallandShamir,1980)从回归到对反政府抗议活动使用强制手段的“数差”(residual,挑战与强制之间的差距)中,发现了一个测量国家压制倾向的方法。对政权的挑战的全面性产生了一个测量这一具体程度——权威对挑战反应不力或过度反应的程度——的方法,官方暴力的使用因而也就得到了规范化。一个假定的小的反应数差被当成是严厉的制裁无可非议、情有可原的理由,因为它们是要对一个严峻的挑战作出反应。桑德斯也有着相似的论述,他说暴力的程度需要放到具体背景中(contextualized)去研究,因为政治互动的“正常”模式从一国到另一国都会不同(Sanders,1981,p74)。他因此认为暴力的使用(官方的或挑战者的)应该根据先前的暴力水平(priorlevelsofviolence)来加以规范化。桑德斯的前提看起来似乎是,如果暴力是习惯性的或普遍性的事情,那么它就失去了它的绝大部分意义。这一句话其实是多余的。因为有着暴力历史的、当前暴力程度高的国家A并不表明它就是极度的不稳定;尽管国家B当前的暴力程度要低得多,但仅仅因为它的暴力历史的程度甚至更低,就可以认为它是不稳定的。
无论是采用杜沃尔、夏米尔的观点还是采用桑德斯的观点,这第三种规范化的方式都是错误的。尽管这些学者看来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但是他们的建议接近于在对暴力的使用进行辩护。 他们还把暴力的使用和权力的实施混淆在一起。是的,暴力可能会引起暴力,但是这一情景已经在许多研究中被模式化了(比如Hibbs,1973;DuffandMcCamant,1975;Weede,1981)。对以相互敌对和先前自己的暴力水平为背景的不同的暴力形式加以规范化、正规化,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基础。
简单地概括,有关合法性的资料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加以处理。特别的是,应该采取什么最佳方式来对这些资料进行综合将取决于特定的分析目标。不管是通过人口规模还是先前的合法性程度来实现,对资料的标准化、规范化的问题也是如此。尽管他们难免有误差和错误,但是这些资料表明了那一时期民族国家政府及其挑战者的暴力使用情况。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去对那些方法加以改进,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那些改进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本书的部分目的就是要为这种努力进行辩护,并强调这样做将会产生的结果。
第六部分 国家政治能力的度量第35节 小结
在本章中我根据制度能力和合法性,界定了民族国家政治能力的定义,并指出了它的度量标准。对政治能力的度量是根据法律意义上国家的年龄和实行宪政的年龄、以及宪政时期内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数目来进行的。对合法性的度量渗透着我在第二章中介绍过的权力和暴力的区别。在那里,我把合法性政体界定为不借助暴力手段就能引导出服从、没有遭到暴力挑战的政体。当然,度量可能不太准确,但是本章讨论过的那些资料确实允许在各国的国家政治能力之间进行广泛的比较。尽管这些比较包含着数量上的排序,但国家政治能力总是一个“度”的问题。
我的目标是要通过把一般性的定义和明确的操作指标连接起来,对有关国家政治能力的集中研究提供一个轮廓分明的图景。许多早先关于发展的研究方法,并没有以一种易于进行系统性的度量的方式来进行,而当今关于国家力量(strength)的研究已经巧妙地避免了这样一个度量上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建立在这一看法的基础上:这样一种策略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以一种持续的方式来衡量一个概念(或者根本不是衡量它)是准确的,但它更容易导致一种虚假的认识并得出一个虚假的结论。与此相对,近期有人断言(Evans,Rueschemeyer,andSkocpol,1985;Mitchell,1991),在我们对民族国家政治能力或国家力量作出一个一般性的表述之前,我们需要有一套明确的经验参数,这样我们才能判断这一进程。 当然,正如我自始至终强调的,系统性的标准的确认,有助于减少,但很难消除所有的定义上的模糊性,误差也就得以继续保留下来。这一过程的优点在于它迫使每个人都直接面对并解决那些问题。
在本书不同的地方,我都强调过我采用过的方法和角度都依赖于或者背离于前人的研究。在最后一章,我将把这些问题置于特定的环境中,并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七部分 结论第36节 结论(1)
“把它写下来”,国王对陪审团说,陪审团赶紧把所有的三个日期写在他们的记录本上,然后把它们加起来,并把它们换算成先令和便士。
——路易斯·卡洛尔《艾利斯仙境历险记》
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对国家政治发展或政治能力的研究写出一个新的概要。政治发展或政治能力这一课题,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部分时间里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然而政治发展研究是从日益增加的攻击中走过来的。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它们被攻击为保守、幼稚和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色彩。同时,它们因为经验缺陷而遭到攻击,人们常常怀疑它的可靠性,因为世界并不与政治发展研究中采用的模式相一致。
事后看来,这些批评很难令人信服。第一,事实是批评家们并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更有成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替代性的研究计划。更为明显的是,尽管人们对国家的研究兴趣再度高涨,但国家的概念深深陷入了一个定义模糊混乱的泥潭。这种混乱影响到所有创造新的方法的努力,以致批评家们只不过提出了一个退回到历史主义中去的建议,并否认一般化、普遍化是可行的,甚至否认一般化的价值。第二,发展研究的著作常常受到攻击,这表明那些研究在批评家看来是故步自封、止步不前的。发展研究被看成是现代化理论学派的一个分支,它把发展当成是不可阻挡和不可避免的,并忽略政治冲突,假定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走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路。但是,这种看法也只不过是一个陈旧的观点,还是一个容易误导别人的观点。
对早期的发展研究我并不是完全赞成。正如对任何一个新领域的探索一样,对发展的探索提出的问题之多超出了它自身回答的能力,而且它们确实包含着许多虚假的起点。它们对第三世界政治发展前景的相对的乐观主义,和与非殖民化运动(此后,这一运动就逐渐销蚀了)相联系的更宽广的激情是一致的。要就应该如何定义和测量发展达成一致意见,事实证明这是难以办到的。 但是这与批评家们的观点远远不同,批评家们坚决认为早期的政治发展研究是完全被引错了方向并因而需要彻底放弃。相反,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尽管发展研究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其中还是包含有很多我们能够加以利用的有趣的见解的。
此外,最近三十年的历史强化了那些观点的重要性。如果说早期的许多研究倾向于乐观主义的话,那么近年来的情况提则醒我们政治秩序的脆弱不堪。在诸如伊朗、黎巴嫩、南非、斯里兰卡那些不同的国家,以及前苏联的残余及其保护国,政治能力是有限的。那也就是说,它们在以政治方式来分配有争议的利益上的能力是有限的。相反,国家有求助于暴力来作为解决冲突的机制的倾向。它们越是这样,它们分配利益的权力就受到越大的侵蚀。在第六章中,我们通过资料表明了那些实行宪政形式的年轻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普遍性。无论人们是否因那些资料而萎靡不振,他们都强调,很多国家在政治上是如此的脆弱以致无法对它们实行有效的统治。这里包含的问题是不言而喻的。
我已经说过,政治能力有两个相关的一般性的组成部分:组织年龄和合法性。从更宽泛的意义来说,这意味着我同时对组织意义上的制度和领袖能够产生的服从和同意都加以关注。我对两个组成部分都予以强调表明,政治生活的核心是权力的实施,而且它不象物质暴力,权力的实施是具有相关性、依存性的。尽管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实施物质惩罚和制裁,但是它们实施权力的能力却是政治能力的关键要素。在这一情况下,暴力的持续使用反映了权力的丧失,而且根本上是非政治的手段,因为它意味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恶化和解体。
这个在第二章中已经讨论过的不成熟的观点,对我们定义和度量政治能力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组织年龄是重要的,因为它体现了制度的调适能力(adaptability)。年龄长一些的组织不仅更可能生存下去,而且,在它们被看成是一直存在着的这一意义上,更可能被相关的人所接受。在这一层次上,年龄间接影响同意。但是仅仅年龄并不意味着能力,对合法性的度量是要更直接地处理同意这一问题。一个政权如果大规模地使用暴力或压制,它就不可能以代价较低的方式获致服从。而且,挑战者通过非正规的渠道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已经不相信能通过正常的政治渠道较低代价地实现自己的利益,并对正规的政治渠道失去信心。
如果我们接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粗略的区分,那么通过集中关注两个集团的行为,那些变量就能以相关的标准来对政治能力加以分类。对于组织年龄的度量标准而言,这种分类是模糊的;对于合法性而言,这种分类又是明确的。当然,那些度量标准并没有解决产生同意的方式这一问题,但是指出了政府可以使用的不同方式。我在第五章中说过,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产生同意的程度问题,这正是那些变量试图要确定的“量”的问题。
我自始至终清楚地表明我的方法利用了早期发展研究的一些成果。毕竟,政治能力常常被视为是发展征候的一个部分(Pye,1966;Coleman,1971),而调适性也被看成是制度化的一个关键要素(Huntington,1968)。制度的持久性(durability)、公共秩序、合法性和决策效率(decisionalefficacy)被爱克斯坦(Eckstein,1971)用来界定国家政治绩效(politicalperformance)。在大多数相同的传统里,扬(Young,1982)认为发展或绩效有六个组成部分:经济增长、平等、国家自治和自立、个人尊严的保护(体现为国家压制的不存在)、参与和“社会”能力(societalcapacity)。
但是持续性不应被过分夸大。在政治发展这一总的项目下,早期的著作典型地认为政治发展包括很多特色。相反,我更为关注把政治能力这一问题从与工业化相连的变化(比如复杂性和分化)和政策结果(比如经济增长和平等)中分离开来。在这一意义上,我的方法比早期的大多数主张限定得更为明确,即便它也由许多部分组成。当然,国家政治能力看来对公共政策和社会变迁问题有着明确的密切关系,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把它们混淆在一起的理由。能力关注的仅仅是政府的程度,需要用自己的标准来处理、分析。
为了对组织年龄进行描述,我考察了根据地理区域和根据国民财富划分的组织年龄的差别,说明了组织年龄并非国民财富的一个简单的因变量。尽管如此,我还是明确反对以系统性的方式去对国家政治能力加以模式化。这种努力集中关注政治能力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而反对把政治能力的不同要素平均化为总体能力的一个简单指标。 此外,这种努力还考察那些组成部分的前提条件和结果。沿着这一思路的分析有很多地方需要指出来。我没有这样做出于三个考虑。
第一,正如我在第六章中提到的,至少,从根本上,那些资料的质量应该有所改进和加强。那些有关政府使用制裁手段的信息被当成是国家压制的一个指标,这是事实。这一度量标准的优势在于,它对合法性的短期波动反应非常灵敏,这特别有助于认定老牌国家权威的衰弱。再说,这一度量标准对于各国之间暴力使用系统性的、长期性的差别的反应就没那么灵敏了。但是正如我指出的,要更全面地收集关于压制的资料是困难的,大部分原因是由于那些材料的政治敏感性。 它已经认识到,那种行为正说明了他们没有能力通过合法渠道来政治解决冲突,正因为这种敏感性,反过来体现了政权掩盖物质镇压手段使用事实的企图,。而且即使有了这些困难,对政府制裁的度量当然优于那些——对自己讨厌的政体就百般指责,而对自己偏爱的政体就百般偏袒——凭主观印象标准来对政府压制进行的度量。
第七部分 结论第37节 结论(2)
第二,在对国家政治能力的各个方面进行模式化处理时,人们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例如,有很多经验研究性的著作都从比较的角度对大众政治暴力进行了全面的、丰富的考察(Russett,1964;Gurr,1968,1970;Hibbs,1973;Weede,1981;Muller,1985;MullerandSeligson,1987)。这些研究中有许多对暴力性的政治挑战和政府镇压之间的关联进行过考察。军队在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受到了很多关注(比如,Jackman,1976,1978;ZukandThompson,1982;HannemanandSteinback,1990;LondreganandPoole,1990)。既然成功的军事政变能够说明宪政秩序的瓦解,沿着这一思路的研究将对组织年龄问题产生直接的影响。 这样,对大众和精英政治暴力的现有的经验性研究,就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研究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是我们研究的起点。但是,那些对暴力的研究的直接动力,主要来自各个层次上的绝对频繁的政治暴力,并来自人们试图研究许多政治秩序存在的并被忽略了的弱点的渴望。我提出的框架为这些分析研究提供了一个宽广、具体、牢固的分析背景和环境。
最后,我并没有去建立一个政治能力的经验分析模型,因为我提出的标准和原则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得到运用,每个不同的方面都意味着一个不同的模型。这些标准和原则能够在这样一个宽广的比较分析框架——它试图证明自己是一个相对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模式——里得到运用。对于限定在一两种情况的更具历史性的研究里,它们是相当合适的、恰当的。而且它们还具有许多其他的潜在的实用性。比如说,我度量的组织年龄,指的是截止到1985年年底的制度,我们很容易想象,为了其他的目的我们需要收集不同政治时代的更多的关于组织年龄的资料。确实,近来发生在前《华沙条约》组织中的许多成员国的事件说明,它们采用了一套新的宪政秩序。我在本书中的目的并不是要研究这些资料可以在哪些不同的方面得到使用,毋宁是要处理有关国家政治能力的定义和度量等一般性的问题。
在不同的地方,我强调过政治能力应该以一种连续性的眼光来看待,并把它看成是一个程度性的事物。这说明不存在一个象充分发展了的政治实体一样的东西,即使在理论上去想象这样一个政治实体,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对经济发展的探讨并不表明潜在地存在着一个充分发展的经济,只是说可以根据各国的经济能力来对它们进行排序。政治能力同样如此。经济能力是指产品和服务的产出(以及这些产出的效率),政治能力是指不借助物质暴力解决竞争性的利益团体之间冲突的能力。换句话说,它指的是消除问题的能力。
如果在比较学家(comparativist)中没有一种普遍的把国家划分成几个独立的、等级式的类型的分类学偏好,如果那些比较学家没有这样一种把排序最前的国家类型看成是代表了绝对的终极价值的总的倾向,那么政治能力总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这一观点就是一个简单而又迂腐的观点。如果我们把这一观点和“使用‘发展’这一词语是一种目的论的表现”这一相似看法联系起来,那么这些偏好和倾向就误导了许多人,使得他们认为,发展是一个要么一无所有要么包罗万象的绝对的、极端的东西。这种观念推动应该得到压制。正如我自始至终认为的,把政治发展这一词语当成是政治能力的同义词是最好的选择。
和我的其他相关的观点一起,把国家政治能力当成是一个连续性的东西这些观点,表明政治能力是脆弱易变的。在特定的国家,政治能力是一个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相当波动的“量”,即便在相对正常的环境中也是如此。正如第六章中的资料清楚表明的那样,国家政治秩序的崩溃并不鲜见。此外,政治能力这一词语的使用并不表明它是一个不容变更、不容逆转的进程。
可能有人会看到我的主张和亨廷顿关于政治衰朽(Huntington,1968)的观点之间的类似之处,确实,我们这两种观点都赋予政治制度以极大的重要性,并极为关注那些制度的脆弱性。亨廷顿把政治衰朽当成是参与和制度化之间比率的一个因变量,即是说,如果参与超过了制度化的能力,那么政治衰朽也就发生了。这样,保持稳定的关键就是,确保参与水平和制度化之间的平衡。亨廷顿对平衡的强调看起来和我对政治能力相关实质的强调有着某些共同之处。
尽管其间有着这些类似之处,然而,我对权力和暴力的区分以及对政治参与如何看待上的观点与亨廷顿的观点大相径庭。我认为,权力的实施事先假定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和合法性的存在,而且对暴力的持续性的依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非政治的(apolitical)。相反,亨廷顿断言,军队——在所有政治秩序中体现暴力使用的组织——能够发挥与众不同的积极作用。请看:
军人干预……常常标志着一连串政治暴力的终止。从这一意义来说,它明显地有别于其他社会集团所能采取的手段……在一个激进的普利夺社会中,军队至少有能力使秩序短期内得到恢复。军事政变是反对政治权威的直接行动的极端手段,但它也是使其他形式的反对这一权威的行动暂告结束的方法,它还是重建政治权威的潜在的方法……在这一意义上,夺取权力,表明了政治斗争的终结,同时它还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正如民主国家里在选举之日发生的情况一样(Huntington,1968,p216-219)。
这种表述当然加上了“短期内”这样的限定词语:很明显,亨廷顿并不把军队当成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即便如此,他的结论意味着,军事政变以及其后的压制性的军人政权,能够把问题解决的方法强加在相关的集团之上并获得成功,而其他的力量是无法做到这点的。而我对此持完全不同的看法,那种军队强加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实际上根本不是有意义的政治解决,从长远看来尤为如此。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通过军事政变就任的政治领袖,他的任职期限也要比其他的领袖要短,并且也可能被另一次军事政变推翻(请参HannemanandSteinback,1990)。这就是为什么多数军人政权最终必定失败的原因。
在大众政治参与的问题上,这两种观点也截然不同。亨廷顿认为在制度较为脆弱的地方,需要对代表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的政治参与加以控制和约束,以使它不致过量。他继续认为,过量的政治参与只会导致政治衰朽和普利夺主义的出现。我在第五章已经提到,亨廷顿的这一结论建立在迪尔凯姆把政治暴力当成是非理性的和社会失范所致的这一假设的基础上。但是这些假设是容易误导人们的,尤其是因为它们忽略了对于采用政治暴力策略的人而言将产生的成本和代价。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把政治暴力当成是一种策略。这样,这些前提假设最好是予以抛弃,并应把政治暴力当成是一个与不同的成本和潜在收益相联系的策略和手段。这样,暴力就不再是社会失范的非组织化的表现,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是那些——认为尽管这一手段可能有很高的成本,但它也会产生收益——人的一种行为。这样来看,暴力行动的发生表明国家共同体的相当一部分人对正常的政治渠道失去了信心,因而它也表明国家政治能力的失败。
鉴于这种差别,很明显,这两种观点有着根本不同的政策意义。当然,二者都强调制度的实际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的重要性,但是那些年龄是一个不能迅速形成的“总量”,即使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如此。那么政治能力如何在短期到中期内来扩大和发展呢?亨廷顿认为,必须对动员和流动进行限制以避免出现过量的要求。但是必须认识到“控制(containment)”这一词语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因为控制的努力会退化为压制,尤其在军队直接地、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治行动时更有可能。
我的观点是,如果人们真的关注政治能力,那么他就会发现控制战略将产生相反的结果。相反,对于新兴国家而言,合法性倒是一个需要迅速最大程度地予以加强的东西。决定使用压制手段是政权可用的基本方法,而最大程度地扩大合法性则意味着它们可以避免物质强制手段的使用。我已经指出,政府可以用包括物质和象征刺激组合在一起的方法在内的各种手段来引导同意。即便如此,合法性产生的难度也不应有任何的低估。正因为认识到这些困难,我才不是一个乐观的预测者。但是,它确实提醒我们,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秩序是脆弱的,而这有助于解释当今许多国家政治衰弱的原因。
-
-
本文地址:[https://www.chuanchengzhongyi.com/detail/40495.html]
不需暴力的权力
• 生活常识
- 本文地址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